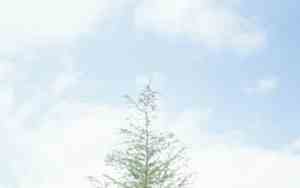1981年8月17阳历生八字(1981年8月17日是啥命)
[147]我的青年与梦乡·第一记丁玲1982-2022
【传媒故事类话题】延安文艺录:在您心中啊[002]
李兰颂
一
这件事已经完全消逝了。它也绝不会再轻易重现。有几个人的名字被长期排列在一起,连他们的子女、甚至子女的子女,也都等同分享由这种命运所决定的荣辱毁誉。
一位我既很陌生又极崇敬的阿姨,曾经被“帮之流”诬陷为“大叛徒”。我去信问父亲。老人显然愤懑到了极点,在回复的信封上公开写到:“丁玲是革命的,是好人!”
接着,是我和父亲分别十三年后在北京重逢的日子,来看父亲的人很多,都问到丁玲,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有一天晚上,我陪父亲在画家彦涵的后海家里作客时听说,香港一家报纸抢先发布冯雪峰、丁玲、江丰、彦涵等四人改正的报道、肖像插图,彦涵评论:“把丁玲同志画得像一个五四时期的女学生⋯⋯”他又说:“也不知道她目前在哪儿?是长治、是京郊、还是黑龙江?”
后来,我在哈尔滨果真盼来并拜望了几位有大成就的作家和诗人,都是父亲在延安时期一起住过窑洞的战友。最早有塞克、萧军、舒群,后来有艾青,却没有丁玲。丁玲是在1981年77岁时才重访阔别多年的北大荒的,途经我们这里来去匆匆,没有给更多人见面的机会。
但是,至此,我却平生第一次得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在书籍报刊上和广播电视里,听她的消息,看她的录像,读她的著作,受她的影响⋯⋯我期待啊,期待有一天、早一天亲眼见到她!
1980年11月28日、12月2日,父亲李又然给当年他在吉林省立吉北地区联合中学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胡昭写信,胡昭又按照父亲的意思给我写信,要我到北京,一方面替他编书,一方面拜师学画。
李又然:致胡昭
胡昭:《哈尔滨日报》收到。文章你写得很好。
立即给兰颂去信,叫他尽可能快地来北京。告诉他我身体更不行了,赶快得把《李又然的散文》编出来,而那几篇东西不抄完,就无法编出来,希望他到北京图书馆给我去抄来。我已给他信,没有告诉他身体更不行了,怕他迟迟不来,所以你要你告诉他,说我身体确实更不行了!至要至要!
祝康健!
又然1980年11月28日
胡昭:致李兰颂
兰颂:昨晚,接你爸的信,催你去北京——看样子老人神志清晰,身体可能是更不济了。你如果有可能,应该尽快请假去一趟!帮他把文集编好,也是了却一桩大事。
原信附上给你。7月份我去时他就已不能上街,达妮,张罗雇保姆也不知雇没雇成——此次寄报纸时问他,回信未提。
我感冒快一个星期了,没有精力工作。已经感觉到“年龄不饶人”这句话的真切。
你如果去北京,请随时写信把老人情况告我。
德裕同志经常给敦敦来信,指点他。他们搬的新房子在哪里?宽不宽敞?
祝
全家好!
胡昭1980年12月2日
而1981年8月17日,因丁玲刚访问过吉林,胡昭得知丁玲为《李又然散文集》作序已毕,却未得到明确答复,就给当时仍未调回北京而还在哈尔滨工作的我写信,要我替父亲李又然写信给丁玲以致谢。
胡昭:致李兰颂
兰颂:我最近同北京几位诗人,一起去长白山区,上月末走的,今日刚回来。见你爸寄来一篇散文稿,无信。我想,这里的刊物已用过他几篇文章,最后的一篇未用,不如你抄一遍送给巴波,看《北方文学》能否发。也许他们会很欢迎。
见他能写东西,很高兴。
在吉林市遇见丁玲同志。周良沛,代我问她:你给《李又然散文集》写了序么?她说:早就写了,没有回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满意?——该马上请你爸,回一封信给她,或由你来回。她已回到北京,月底去美国。
我一切都好。也许9月初去敦煌,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
祝
全家好!
胡昭1981年8月17日 夜
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近年所著《丁玲办〈中国〉》一书的“第六章/1.对两位老友的深切纪念”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记述丁玲与冯雪峰、李又然的关系时,写到父亲李又然这样说:
王增如:对两位老友的深切纪念
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延安文协时期张仃的夫人陈布文,转来一封李又然的信:
“布文:接到你信。我为什么不出来走走呢?我腿有病,走路困难!现在说话也困难了。整天没有力气。⋯⋯要是能走路,我就来看你们了!丁玲还没有见到。祝贺她一切顺利!”
陈布文是要告诉丁玲:李又然身体不好,但是还在惦念她。
李又然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但个性很强,人生的路跌跌绊绊,很不顺当。他不大合群,不大好交往,但对丁玲始终十分敬重。1973年他从干校回到北京(此时李又然并未回北京,他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李兰颂 注),有一天听人误传丁玲不在人世了,他几乎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屋子里木然呆坐,不发一言。
1981年春天,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散文集,他想请丁玲写篇序言,托人把稿子带给丁玲,写信说:
“我出书不容易的。请你写序好么?请一定写!我本想写回忆录,我有很多好写的,但是没有力气,写不动了!一篇《毛主席》,足足写了几个月!一篇《丁玲》,也得很长时间!但我无论如何要写的!我来看过你,找不到地方,尽管你的地方很好找的。现在不能再来了,因为我在房间里沿着桌子走走,都非常吃力,十分困难了!奈何!”
信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一字一格,字迹有点打颤,写得很吃力。
一周以后,丁玲就把序言写完,不长,只有千把字。她回忆说,初见李又然时,“觉得他仿佛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现在也仍然觉得他挣扎一生,却很少得志,意气洋洋。他总是暗暗地为别人祝福,寂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害人之心的人。”
本来丁玲文中还有“他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样的话,李又然读后,给丁玲写信说:
“序,我珍惜的。我不满意的是自身,缺陷太多了!”又说:“‘他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句话一定、一定涂掉!”
李又然的长子李兰颂读了丁玲写的序言,于1982年2月农历正月初十这天,特意到木樨地丁玲家登门致谢,当着丁玲和陈明的面说:他和弟弟刘华沙(母姓——李兰颂 注)都认为丁玲阿姨短短千把字,把他爸爸的一生、为人都写出来了,他爸爸确确实实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三
父亲李又然实际是及时给丁玲阿姨写过信的,记得最早一封关于“‘他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句话一定、一定涂掉!”就是由我寄出的。
后来,丁玲阿姨为《李又然散文集》序致函二则,被收入《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证明丁、李二人,仍保持着书信往来。
丁玲:致李又然
又然同志:
你的文稿我都读了。当何养明同志把它交给我时,曾说希望我能写几个字。我也一口气答应了。只是当我读后,却感到有些为难了。我对这些稿子,有点肤浅的印象。你的文字原是很好的,现在也仍然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写罗曼·罗兰、艾青的回忆。但为什么又感到为难呢?就是这本集子有点杂。你对科学家的文章是好的。只是放在一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反而把他们给人的印象弄淡了。对毛的回忆,我是绝对相信你的,自然其中也有个别记错的地方,我担心会有人要挑剔你的。写我的回忆,我以为过去你对我还是有意见的。你把那些放在一边,反而说了些我的好话,我谢谢你。在延安文协时,你曾为我跑去桥儿沟看陈明,那种热心,我是从来没有忘记的。但我对你却没有那么好,对你的工作,我向来不愿以友情安排,而且常常对你做些规劝,甚至常常认为说得不够。对你的生活也是不怎么关心的。所以我以为对我的回忆实际可以不放进去。你的身体不好,还多少写点东西,已经不坏了。还是希望你保重。请原谅我。
稿另附上
夏安!
丁玲1981年5月27日
又然同志:稿子放在我这里很久了。今天才写出几句话。请原谅。
稿子奉回,请查收。
我写得不好。你如觉得不适宜,可毁之。如觉得可用,则用之。
祝好!
丁玲1981年5月30日
在此前后,为了急切地将书编起来——就是将《李又然散文集》编起来,父亲甚至连续地写信叮嘱和催促我:
李又然:致李兰颂
兰颂:
信和艾青的《诗论》都收到。丁玲到鼓浪屿去过,茅盾追悼会赶回来。序,她写的,不过要等着,因为她常有病,又很忙。萧军那里你自己去封信谢谢他送书。他住鼓楼西烟袋斜街鸦儿胡同6号。
你在参加学习,这好的,用心学!
祝康健!
又然1981年5月1日
兰颂:丁玲的序立即抄一份来!立即去抄,立即寄来!至要至要!
祝康健!
又然1981年7月16日
兰颂:告诉出版社:
1.封面全白,不用任何图案;红字,仿宋体:
李又然散文
丁 玲
序
陈企霞
2.清样一定寄来看过!
3.目录上《光荣属于红军》(抽掉)、《我们大家的两个家》(抽掉),是否可以补上!现在译苏联的作品越来越多,有一份期刊就叫《苏联文学》。
4.何时出版?
5.盼即复: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印研所转李又然。
***
你如太忙,不能去,此信可加封贴邮票寄去。
祝康健!
又然1981年8月7日
兰颂:《伟大的安慰者》,我抽掉两篇,补上十多篇和丁玲的一篇序,上月底挂号寄给你,是挂号寄的,想来不会遗失,那么今天已是11月11日了,怎么还没见你的回信呢?很挂念!望速见告!
祝康健!
又然1981年11月11日
四
李又然最早写丁玲在上海。1933年5月14日,丁玲、潘梓年在上海昆山路丁玲寓所被特务密捕;同日应修人在丁玲寓所遭特务追捕,搏斗中坠落牺牲。“丁玲等:或失踪,或睡在黄浦江底。”这是李又然题为《PROLOGUE(雪底下的火山)》(1933年7月1日第15期《出版消息》)文中最末一句,是他第一次提到丁玲名字。
丁玲是李又然在延安加入中国的二位介绍人之一,另一位介绍人是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江丰。而丁玲和李又然,从延安分别后三年,进入解放战争的后期,在沈阳相遇,又很快相继会师北平。1949年3月19日,在沈阳,丁玲日记(摘自《丁玲全集》第十一卷·日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写道:
丁玲:日记1949沈阳
下午刘芝明来。伯夏(陈明)和他谈剧本提纲,他也提不出多的意见。我同他谈文协的事,他说有两个方案,一是我做,一是徐懋庸,已请中央去批了,我想中央是不会同意我的,而且徐较我要好,我还是写文章好。
今天本来打算和伯夏出去玩的,因为李又然和魏伯要来看我。他们来坐了一会,他们要去北平。魏伯是连部长也不够味,他做的事真多,改行真改对了。
李又然不过换个地方,他仍会不如意的,仍会牢骚的,他的神经是有病的,这种神经病是由思想上不能解决问题,而问题又多的缘故。他不过是较轻的神经病,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地道的好人!
晚上看工人剧团演《废铁炼成钢》,演得真好,那个演二流子的演员实在是天才。演工会主任的也好。剧本虽然拖拖拉拉,但看来非常舒服。
在此前的十几天——1949年3月6日,也在沈阳,胡风日记(摘自《胡风全集》第十卷·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写道:
胡风:日记1949沈阳
……
李则蓝来(李又然在东北时使用的化名),谈到3时,共四小时以上。
○周扬主张《桑干河上》不能出版,因为程仁和黑妮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说这作品好,周的看法(或意见)是错的,且由、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保证。
○劝我在宣传部做点小工作,学习一个时期。
○不应向真诚的青年随便谈人事上的意见。
○在整风时(初期),“胡风进来了多么好”。
……
这个时期,、八路军作家们的全新创作,对于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十四年之久的东北青年,该是多么如饥似渴的精神食粮啊,父亲李又然对待同志、战友如此,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也是如此,他要送给他们阅读最新最好的书。胡昭就是一例:
胡昭:“我能留给你的不是珠宝⋯⋯”
我还是在上了初中以后才知道丁玲的。在同学中传看的一本揉皱、摸脏的小说集里,我读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一个孤独的女性的苦闷与挣扎;接着又读到写农民反抗斗争的《水》。这是代表她不同创作时期的两篇名作。说真话,初中学生的我不大能够理解。——尽管如此,丁玲对我来说是崇高的,又是亲切的:第一因为她是我们八路军的大作家之一;第二因为她是我们校长老师李又然的朋友。丁玲来到东北解放区,她在哈尔滨,她在沈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1948年末,李又然老师主持吉林文协工作时编辑出版《文艺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片断《拔大旗》,写的是华北土地改革,我读来倍感亲切。
全书出版时,我已在吉林日报工作,李又然老师又奉调进关。在北京,又然师同延安时代的许多战友相遇了。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又然师寄来了丁玲同志的书,这是作者签名送他的,他转赠给我,在书上写了几行字:我能够留给你的,不是什么珠宝,不是银行存款,而是比这更宝贵的丁玲同志的书。并请丁玲同志题了字,记得意思是:又然要把此书转送他的朋友胡昭,嘱我写几个字。我只想,这部书不是我的最后目标,它只是我向目标走去的一个脚印而已。——当时,我在一个边疆小城里接到如此宝贵的礼物是多么高兴啊!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收到如此珍贵的礼物,激动之情很难说清。书是布面烫金的,过去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书。用厚纸仔细地包了皮之后通读一遍,以后就在同志中间传阅开了。这部书荣获斯大林奖金,我们觉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共同分享了这一光荣。
五
1982年,农历正月初十上午,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买元宵的人随处可见,朔风呼啸,偶尔,还伴着几声爆竹的脆响,吹入了我的耳畔。我在木樨地一座高层楼厦,乘电梯在九层的一隅单元叩开门,被一位叔叔迎进客厅,我猜他是陈明。很快,丁玲阿姨由内室里带着笑声轻缓地走来。我们会面了!握手了!刹那间,我心里,蓄满了她通过双手传达给我的温情⋯⋯
“我现在是满腹文章,只是感到时间不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落座后这样说。她的语调平稳、自然,普通话略带湘音,她说:“你爸爸,我几次想去看过,很多老同志都早该去看看,可是我每天都在抓紧时间,也可以说是抢时间写作。为着千千万万的烈士,为着我们的幸福的后代,为着我们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有责任、有义务奋起我最后的余力。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昏昏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
我惭愧自己平日怠惰而今天又冒昧来打扰她;她安详自若、从容愉快的神情又宽慰着我,使我倍加珍惜这次会见,集中心力倾听她坦率诚恳、娓娓道来的话语,并想以此作为我最珍贵的回忆⋯⋯
我没想到,她这样问:“你结婚时怎么办?大办、小办?不办?”她又似乎在答:“爱情既不是低级的享受,也不是高级的罗网。新时代的青年,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是会懂得怎么认真地、正确地处理个人日常生活、和比较细致而深沉的感情生活的。你说起婚姻介绍所,我觉得它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解决‘大姑娘和大小伙的困难’,介绍只是介绍认识,代替不了恋爱。介绍之前,对双方要有相当了解,相信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再介绍。恋爱是火啊,火是不能随便玩的,更不能当成商品,要深刻、严肃、专注才行。即使在婚后也还要把恋爱保存、培养、发展起来。婚事一定提倡新办、省办、简办。我们那时都不办!喜事嘛,热热闹闹,怎么可以举行集体结婚典礼也花很多钱?也回去再办?”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她如此详尽地熟悉下情!她是一位多么正直纯朴的战士、慈祥温厚的母亲啊!
六
“您今年78岁吧?丁玲阿姨!”我问。
她稍微动了一下右手的中指说:“我大你爸爸两岁,生在中国最黑暗的清朝末年,1904年。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不管怎么说,怎么比较,你们所处的时代总比我们当年的更优越的多。你们自然也会有你们的困难的地方,逆流搏斗的不乏其人,思考的、奋起的占大多数。但自卑的、垮掉的也有,这样的人总嫌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他们哪里了解一点点外国的真实情况!就说美国吧,我刚才那里回来。那里有许多好处,我该说些好话;可是,它却以它许多浓重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喘不过气来。我会见了尼姆·威尔士女士——已故斯诺先生的前妻,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37年曾不避艰险,越过的严密封锁访问延安,写成《续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领导下的解放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我们对这位老朋友一直是怀念的,建国后,她曾两次应邀来访。她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出国的留学生,一个月除开学费、医药保险等,仅食、住两项也发给360美元。她呢,一个孤身病老的人每月才120多元,光电费就要交付175元,暖气都舍不得烧!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日子。她有32本尚未出版的手稿,可是她告诉我,“这儿有中国几乎不可能有的最坏的审查”。看看吧,我们老少两代人都能在这面‘镜子’中照出我们的幸福,照出我们光明的祖国。”
我被丁玲阿姨的谈话激动得热血沸腾,问话就多了,嗓音也大了,“丁玲阿姨!”我说,“可是现在一谈到对国家大事不关心,对学习马列不认真的问题,总有人将一股脑的怨气都推给青年,这样说能对吗?”“我坐过五年‘’的监牢”,丁玲阿姨深有感触地说,“就在这时候,我通读了‘马恩全集’。到了1975,隔壁牢房的人都放了出去,我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唉,让我读完这部全集再放我出去吧。那么出了监狱不能读吗!脑子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世界上什么是最好的书哇?我看就是这本书。什么人是最好的人哪?最有智慧、最有感情、最高尚、最可爱?那就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可惜我在牢里没有条件作笔记。可是你们呢,不要像我等坐监牢才读,时间‘挤’才能有嘛!这部书真是百科全书,最好的书。我看青年们要是真的读了肯定爱不释手,保险有收获。至于无端地抱怨青年可是不对的。这些话,我给讲习所的学员们讲过,讲得挺多。”
七
“怎么,您去讲习所讲过课?您还记得最早的学员胡昭吗?”“胡昭这些年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听到我的问话,丁玲阿姨立即这样说。“胡昭等我认识的人都常说起您呐!”“可是现在讲习所还没有好房子,学员的食宿条件也很差⋯⋯”“您知道不少地方办了五花八门的班⋯⋯一个个可能收钱了!”“教学收费没错,关键看对学生是否真正负责。我要是能空出一个房间来,我还准备办一个班呢!星期一我教文学,星期二我女儿教舞蹈,星期三我儿媳教声乐⋯⋯”
她越说越有兴致,那样一丝不苟,就像在开学盛典上发表演说。我也越听越觉振奋,那样信以为真,竟忘记把刚带上楼来的一张《文汇报》,拿给她看。有则当日新闻说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著名芭蕾舞剧编导蒋祖慧,热情指导天津歌舞剧院排练演出大型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在天津市文艺界传为美谈⋯⋯祖慧,革命圣地延安长大的舞蹈艺术家,丁玲阿姨的女儿!丁玲阿姨“教学计划”中的“老师”!
“我先知道您要办班,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我要搞入学考试,并且也收学费哟!”丁玲阿姨边笑边说,如此一往深情而又含蓄幽默。“你第一次来,来一次又多么不容易,”转过头,她告诉陈明叔叔,“拿几本书给他带回去!”我起身走到丁玲阿姨的近前,看她潇洒地挥笔在书的扉页上题名留念,一本一本,一共六本,陈明叔叔和蔼地告诉我哪几本是再版的、哪几本是新作——它们各自怎样标志丁玲阿姨创作道路的几大阶段⋯⋯
此时给我极深的印象是丁玲阿姨的笑容,我想,我真的这样想,她的笑,就是她的心,她的心就是她的人。她动手术不久,外事频繁,著作等身,和我这个小字辈谈起来就是一小时,尤其在我告辞的时候,我们三人站在客厅中间地毯上,丁玲阿姨握着我的手,叮嘱说,“回去好好干!别辜负父辈的培养!再呢,给你爸爸搞个轮椅,能让他经常出来晒晒太阳,也可以多活动!”
她甚至说:“也转告你妈妈,没必要太封建,让她和你爸爸复婚,把被搞散了的家复合起来,相互也是照应。”母亲刘蕊华,是丁玲任所长、李又然任专任教员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的研究生,是二人的学生,所以丁玲阿姨才这样关心和率真地叮嘱。
陈明叔叔拍着我的肩,温抚着说道,“回去告诉你爸爸,说丁玲阿姨见到你后非常同意删去为他书作序时提及的那句话,你多么年青啊,多好,我们当中没有谁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此刻再看,丁玲阿姨,陈明叔叔,会意而欢快地握起手来,这依恋动人的情景我真像在哪儿见过一样?
啊!我见过!见过!是在《“牛棚”小品》里,是在《三访汤原》里,是在陈明叔叔冒着极大危险投给丁玲阿姨的一个个小小字团里⋯⋯
“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看啊,丁玲阿姨,您和陈明叔叔几乎送我到电梯口了,请回吧,再见吧,我心中永远有您:党的战士、青年的母亲!而您,在您心中啊⋯⋯
八
拜见丁玲阿姨之后,我的心情是激昂澎湃的,我想写这访问记,但觉得话语太多反而无从下笔,我就连夜阅读她送给父亲的厚厚的六大本书,很快我回到工作岗位,父亲却连续写信催我,这也是他给我的绝笔,一生中给我的最后两封信:
李又然:致李兰颂
兰颂:你已经到哈尔滨了吧。陈学昭回信还没有到。你该结婚了。有朋友吗?爸的诗,始终编不起来,因为有些诗在一个朋友那里;几次去要,却始终没有寄来,也许找不到了。
《丁玲访问记》赶快写一写!
《战争与和平》立即读一读!
写了、读了之后都一定告诉我一声!
祝康健!
爸1982年2月10日
兰颂:为什么一直没有信来?
《丁玲访问记》写了没有?
《战争与和平》读了没有?
祝康健!
又然1982年3月25日
《丁玲访问记》,是父亲李又然一生给我的最后两封信中专门为我出的作文题目,而我终于将这篇访问记脱稿并发表的时候,父亲已经谢世,这篇所谓的“丁玲访问记”,题为:《您心中啊⋯⋯》,另外,还有一个副标题为:“——丁玲印象”。
那篇发表过的《丁玲访问记》有五点没有写,这里记下,待日后补:
1、历史50年以后写才更客观,你爸向毛建议,是对的,应该说;
2、我们(丁玲、陈明)忘不下,在延安,你爸为我们传递情书;
3、告诉你爸爸,不要理陈企霞那个坏东西。
4、有神经病,还是健康?
5、冒舒烟写悼文要我给丁家打电话,陈明叫我到会上散发讣告。
九
这就是丁玲为《李又然散文集》所作序言全文:
丁玲: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说在“”得意的年代,有一位同志也凑上去了,准备歌功颂德,写篇文章以示忠心。可惜遇到一点意外的事,文章还未脱稿,而10月6日那天,“”陷入汪洋大海,他却脱险了,且还有了摇身一变的机会。真可谓塞翁未失马,免祸又得福。世界上总有许多人是有福气的。看来这种福也要费尽心机,得来不易。但另外有些人,总好像在穷愁中过日子,长年给人以穷愁潦倒的印象。我初见李又然同志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仿佛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现在也仍然觉得他挣扎一生,却很少得志,意气洋洋。他总是暗暗地为别人祝福,寂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害人之心的人。是一个弱者,但也是一个强者。
我知道,我这样说,李又然同志是不会同意的。他自己觉得,而且常常觉得他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他不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而是常常怜悯他人的人;他是一个自豪的人,他会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很大方,很高傲。然而我总还觉得他需要同情,需要温暖。他给过别人爱,给过别人同情,给过别人温暖,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很少。(他一定又要反对我这样说了。)胡考同志曾经称他为“姑母”,意思是他像狄更斯小说中考柏菲尔的姑母。我以为这是恰当的比喻。可惜的是,这个姑母却生在20世纪的中国,随着革命的进程,经历了多次的运动,和灾难的十年,他现在是瘫了,病了,出不了门。他只能从报纸期刊上关心着跟随着革命和新的、旧的朋友的踪迹,踽踽前进,看着世态的多种变化,更深刻地体会着先圣先贤们给我们留下的许多至理名言。
但这只是一方面。李又然同志确实年青过、忙碌过,生活得很充实。我记得大约是1941年,我们住在延安边区文协的时候,他在女大教世界语,还兼女大业余文学小组的辅导工作。有一天天刚亮,我站在窑洞外面,看见他急匆匆地往山下跑去。我问他:“李又然,这样早你忙着到哪里去?”他回答:“到女大去,昨天我给她们写了一张墙报,半夜想起错了一个字。好容易盼到天亮,这就赶去改正。”我说:“吃了早饭去也不迟啊!看你连脸也还没洗。”他一边继续下山,一边说:“那不行,那不行,那就晚了。她们也许一早就会去看墙报的。”后来他回来了,说墙报上的文章没有错字,只是他以为错了,他也并不后悔冤枉跑了一趟。
抗战胜利后,他到了东北,在佳木斯、哈尔滨和吉林联中及大学任校长或教员、报刊主编或文协主任。其中教员工作对他是非常合适的,听同学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员。诗人胡昭同志就曾得到他的教益不少。自然还有许多别的学生;而围绕着李又然同志的,也有不少打心眼里真的对他有深厚感情的人。不过我不十分知道罢了。
我过去,认为他的散文写得很好,这次重读50年代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安慰。原来李又然同志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有健康的饱满的热情,爱祖国、爱人民、爱、爱社会主义事业。他不止具有菩萨心肠,不止是一个“姑母”,而且是一个壮士,一个战士。他的感情是一个战士的感情。可惜后来他没有得到继续发挥的机运,他的身体也确实不很好了。他最近写的回忆录就未免有点显得苍老了。有些事也可能记得不那么准确了。但他同艾青同志少年时代的交往,仍然是非常感动人的,是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
我对李又然同志可以说并不完全了解,但我仍坦然地说了一些我自己的片面的感觉。我愿意向读者介绍他的散文,也愿意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偏见。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1981年5月30日
附记:原载于《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1982年1月创刊号·总第一期),用于《李又然散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后收入丁玲所著《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丁玲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丁玲文集》(改标题为《序〈李又然散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丁玲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包括《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致函二则》均被收入《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