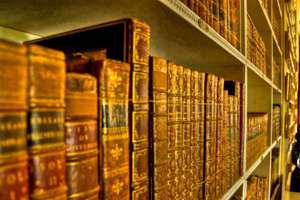阴历1970年7月14日出生八字(1970年农历7月14日出生是什么命)
中国载人航天,你不知道的故事
2022年9月21日,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整整30周年。
不过,我国与载人航天事业的渊源,并不止30年这么简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前,还有一段少有人知的故事。
我国早期载人航天研究
据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介绍,我国在1964年至1966年间,就发射了多枚生物火箭,先后把小白鼠、大白鼠和小狗等动物送上了天,而且所有试验生物都安全地回收了。这些生物火箭试验开创了我国宇宙生物试验的先河,为航天医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6年,我国制定第一个“载人宇宙航行规划”,设想在1973年至1975年发射我国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并开始了我国载人飞船的总体方案论证工作。
在1968年1月召开的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同年4月1日,我国正式组建了代号为“507”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承担有关航天员生命保障、医监医保以及航天员选拔训练的任务。
1970年7月14日,批准实施“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也叫“714”工程。1971年,我国从1000名空军飞行员里选拔出了20名预备航天员,并全面开展载人飞船方案论证工作。
但由于我国当时经济和技术等基础非常薄弱,“曙光一号”飞船工程自1971年10月以后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75年3月,国家正式宣布我国首个载人航天工程下马,把航天发展重点放在研制应用卫星上。
曙光飞船方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和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家从1986年起开始实施“863”计划,其中包括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中国载人航天再次迎来发展机遇。
在载人航天器中,空间站具有体积大、寿命长、功能强的特点,适合长期载人航天开展太空科研工作,但不能天地往返,所以在研制、发射空间站之前要先研制可以天地往返但体积小、寿命短的宇宙飞船或航天飞机,主要用于接送航天员和货物。
当时我国专家就研制哪种天地往返运输器有很大争议,在呼声较高的5种方案中,有4种是研制航天飞机的方案,只有1种是研制载人飞船方案。经过几年的深入论证,根据国情和国力,遵照“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863”高技术研究发展指导思想,专家们最后一致同意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决定不走美苏研制载人飞船的老路,直接研制达到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水平的“神舟”飞船。
实践证明这一决策非常正确。美国花了2000亿美元,研制了6架航天飞机,发射了5架,进行了135架次飞行,但损失了2架,牺牲了14名航天员,最后不得不在2011年提前退役,然后重新研制新型载人飞船。苏联、欧洲、日本也都研制过航天飞机,但在走了一大段弯路后均没有投入使用。
1992年9月21日,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启动。
30年来,我国先后研制、发射了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空间实验室,突破和掌握了空间出舱活动、空间交会对接、在轨加注燃料、航天员中长期在轨驻留等许多关键技术。今年年底前,当“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并与在轨运行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组合体交会对接后,中国“天宫”空间站将建成,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最后一步。
“天宫”空间站示意图
当然,中国空间站的发展之路不仅如此。
庞之浩介绍,我国还将在2024年发射与“天宫”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光学舱。它将搭载2米口径的巡天望远镜,分辨率与美国“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视场角是后者的300多倍,可在大范围巡天科学研究方面显身手。
中国空间站系统还有一大创新:其将成为世界第一个航天器“母港”。例如,“巡天”光学舱在需要时,可与“天宫”空间站主体对接,由航天员对其开展推进剂补加、设备维护和载荷设备升级等活动。
此外,中国空间站还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扩展,由“T”字构型扩展成“干”字构型,活动空间增加一倍。其未来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
来源:科技日报
父女年龄为何仅相差14岁?民警翻了几百个档案盒,终于找到了原因
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百态人生,作为一名专门办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常常要面对彷徨无助的被害人家属,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尽我所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老薛(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11月初,老薛的女儿小敏(化名)在一起刑事案件中遇害。作为主办检察官,我在审查案卷时发现,老薛的年龄存在疑点:老薛的身份证显示出生年份为1979年,而小敏的出生年份是1993年,父女年龄仅相差14岁,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然而据鉴定机构出具的老薛与小敏的亲子鉴定证实,二人确为父女关系。
初次见到老薛,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看起来确实不止40多岁。“我女儿突然就这么没了,她才28岁,检察官,我真的接受不了。她妈妈有高血压,从女儿出事以后就病倒了,下不了床,天天哭。”他向我倾诉他们一家的处境,看着他哽咽难言,我内心也十分难受。
“检察官,我就这一个女儿,我平时种地,出去打个零工,女儿上班挣钱也能补贴家用,日子还算过得去。现在女儿没了,我再过几年也干不动重活了,可是我身份证上比实际年龄小9岁,村里60岁以后发放的养老保险金我到时候也不能正常领取……”老薛告诉我,他真实的出生日期其实是1970年5月17日,但在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误将其出生日期登记为1979年5月7日。老薛也曾想要纠正这一信息,但因年代过于久远,能证明其真实出生年月的信息资料缺失,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随后托鸡泽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王舒敏联系老薛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对方的回复是,我们要找的信息没有电子档案,需要从档案室原始户籍底账中找到能证明他真实出生日期的户籍页,才能帮他纠正身份信息,他们还提醒道,原始底账资料繁杂,想找的特定的户籍页难度很大。
记挂着老薛这事儿,11月19日下午,我在一次庭审结束后,与王舒敏、检察官助理刘晓晨一起来到老薛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虽然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是看到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都是档案盒,每个盒子都装着几百张泛黄的原始户籍页,我们一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这时候打退堂鼓是万万不能的,我们每个人分了一摞档案盒,开始一盒一盒地找,一页一页地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三个人机械地重复着查找翻阅的动作,这时我们听到王舒敏惊喜地喊了一声:“找到了!”我们赶紧凑过去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查到的登记信息依然是1979年出生。正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户籍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1998年人口普查资料,档案室还存有1989年人口普查档案。我们的心里又重新燃起希望,决定继续找。派出所的几名同志也许是被我们的执着感染了,也开始帮我们一起找。
天色渐渐暗了,档案室里气温虽然很低,但我们忙碌得热火朝天,大家的分工协作,效率提高了很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老薛的原始户籍页,泛黄的纸片上明明白白写着,老薛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5月17日。
当老薛赶到派出所,看到我们正在整理堆积在办公室各个角落的档案资料,他激动地眼眶都红了,不停握着我的手道谢。我说:“不用谢,老薛,能给你帮上一点忙,我们很开心。”
群众的事没有小事,也许我们的举手之劳,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个大难题,也许我们的小小善举,能让身处困境中的人们感受到一点暖意。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一次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讲述人:河北省邯郸市检察院一级检察官刘鹏)
来源: 河北长安网
记忆中的物事49,童年
童年真正的记事是从六岁开始的。清楚记得1970年7月14日,一辆老式的解放牌汽车,拉着我家的全部家当,从老随县城关镇二街鹳坑边到随县三里岗镇尚店村火石冲一个叫天子岗的地方,下放农村。那地方是随南大山的深处,当时名称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生产队,那时我6岁。
6岁的我站在货车车厢的前端,迎着呼啸的山风,呜呜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下子从城里来到山野,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似乎突然间,我开始记事了。
再往前,应该都是大人们讲的关于我的故事,虽说不应该算作是我真正的记忆,但那同样是我的童年。
农历1964年正月十四,我出生在老随县城关镇二街一个叫鹳坑巷的地方。之所以冠以老随县,是因为现在的新随县已经迁移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厉山镇。老随县就是现在的随州市区,行政区划属曾都区。
没下放到农村以前,也就是6岁以前,我一直成长在姥姥家里,我把姥姥叫奶奶。
因为我的奶奶早已不在了。大约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即1948年前后,爷爷奶奶就在武汉相继病故了。
这些关于家,关于祖上的故事是从父亲的回忆录里获知的。父亲于81岁也就是2021年开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到83岁去世前戛然而止。当时,我把父亲的回忆录稍作整理,以《父亲的往事》为题共54集,陆续发在平台上。
我家祖籍在老随县下南关,是南关口的邹姓望族。爷爷邹永忠,字季厚,时期曾任过随县县长,在《随州志》里有关于他的记载,在手机百度里搜索邹季厚,也有零星的记载。
爷爷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随县一中教书,1940年前后任县长,后来全家迁居武汉,教书经商。父亲兄弟四人,他是家里的幼子。1948年,爷爷奶奶在汉口长堤街的居所相继病故,当时战事频仍,大伯于四九年九月将九岁的父亲从武汉送到老随县姨妈家,过继给姨父母,改姓傅。
父亲在他姨父母也是养父母家过了十多年,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961年前后,他的养父母也相继病逝了。
因为家族,因为爷爷当过伪县长,因为家庭成份,就是我家下放尚店火石冲农村的直接原因。
孩提记事是从下放农村开始的。下放前,依稀记得我在城里幼儿园读中班,我家住在现医药公司斜对面,这是父亲砌成才两年的一间新房,但我不住这,我住在姥姥家。姥姥家在鹳坑西边的老食品公司隔壁,距我家几十米的一条弯曲的小巷子,儿时带着奶腥气的玩伴只记得院子的罗星罗勇几个名字,其它的物事随着岁月久远都已模糊了。
下放前,父亲在城关搬运站拉板车,母亲在缝纫社做衣服。普通的劳动者,却是令人羡慕的双职工。
依稀记得父亲拉板车时,把年幼的我放在装满高高货物的板车前杠上坐着,上坡时,我在后面帮着推板车;他把“丹江”牌纸烟盒给我玩,他在搬运二站大门前的葡萄架上给我摘葡萄;更多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妈妈的缝纫社,妈妈和许多阿姨同事在缝纫上缝衣服,奶奶戴着老花镜,坐在凳子上帮着锁扣眼。
1970年,城关镇号召上山下乡。因家庭成份问题,我家也被动员下放。当年7月全家下放到尚店红岩大队时,姥姥家已先于我家几个月下放到尚店红军大队了。我们两家之间隔条碾子河相望,相望的距离是走山路大约1个小时。
下放2个月后,我读小学了。当时的学期上半年是上学期,9月1号开学时,小姨把我报名在红军小学,插班一年级下学期。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因为红军小学在尚店街边上,而我家所在的红岩小学却在深山里,所以小姨让我读街边的小学。
因为跳过了上学期,而别的同学已经读过半年,学过了拼音也会写字了,于是我一直跟着拖。到如今,我依然不会汉语拼音。
入学报名的时候,班主任赵权红问我家庭成份“什么农?”我懵逼地说“大龙”,因为我属相大龙。同学们一阵哄笑。那时填履历表,都有“家庭成份”、“个人成份”栏目,在农村,家庭成份有贫农、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之分,所以赵老师会问我家“什么农”。
为此我问过父亲,也看过我家那时的户口本,父亲的“家庭成份”一栏,写的是“未定”,因为父亲在童年时已过继给他的姨父母了,他姨父母生前的营生是商贩,但他亲生父母却是“资本家”。不知道当初给已是孤儿的父亲定家庭成份“未定”是什么原因。
现在早已不提家庭成分了,但在那个年代,如果家庭成分在富农以上,连"红小兵“”“都入不了,升高中、参军、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入党等等,基本也就没你的事了。
记得我入“红小兵”时,是班上的倒数几个;年轻时我曾想参军,到厂里的政工科询问政策,政工干部意味深长地讪笑着词不达意,那已是1981年的事了。这是后话。
红军小学在尚店街东边。每天上学,从火石冲天子岗下沿碾子河走,穿过尚店老街到学校,要走1个多小时。那时只上半天学,中午回家,下午做家务附带照看弟弟妹妹,或是砍柴放羊打猪草。
学校支农是经常的事。插秧割麦割蒿积肥等许多只要是小孩子可以帮忙干的农活我都干过;学校还经常开展“勤工俭学”,捡橡子打桐子挖蜈蚣割黄荆条寻中药材,能卖钱的土货山货我都弄过;学校还经常搞“忆苦思甜”,请老贫农到学校讲解放前的往事,声泪俱下;尚店街上的小广场还有“万人大会”即阶级斗争批斗会,口号声惊天动地;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小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文艺调演”样板戏,还有乡村巡回放电影时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童年最刻骨的记忆是饿。那时候农村普遍都饿,我相信,粮食360的概念于60年代的人都刻骨铭心。好在我家在随南大山里,四时的野果野菜可以帮衬着度过春荒,反倒成了儿时温暖而快乐的记忆。
1972年我8岁时,姥姥家搬到了随县城郊公社胜利大队十四生产队,虽然仍属农村,毕竟已换在县城边上了。一直到返城前的这几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放暑假去姥姥家。这个时候的我,应该称作少年了。
现在打开手机地图,尚店距离随州城区35公里。那时公路没有通车,想去随县县城,须得徒步到均川搭班车,一般早晨天亮开始走,赶在中午前搭车,5角钱车票到随县。
虽然山长水远,却是一段幸福的里程,这段俗称“二十四道脚不干”的山路,承载着我童年和少年最幸福的记忆。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