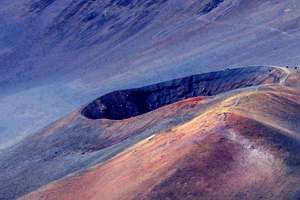1985年六月初四八字
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流动与变异
作者: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在写抄本时代,作者和传抄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种种歧异,如河流般变动不居。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生成、流通、变异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样貌,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异文、乱篇、歧说三个层次,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字异同,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1]。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
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存在的文本歧异,大致可以分为异文(文字异同)、乱篇(篇章错乱)、歧说(歧说异闻)三个方面,它们又是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三个层次[2]。“异文”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在创作阶段,也可能是在传抄阶段。在创作阶段,作者的文集又有“自定”与“他定”的不同;而在传抄阶段,又有抄手和抄写底本等不同原因。我们先来看创作阶段的情况。
(一)“异文”的产生,首先缘于作者自己的修改,属于创作中的变动,是作者本人让文本处于变动之中。众所周知,文章初稿和定稿常常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定稿之前的创作变化,东晋袁宏《北征赋》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刘孝标注:
《宏集》载其《赋》云:“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3]
袁宏所撰《北征赋》尚是初稿,所以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删加工。还有被迫修改(或增补)文章的情形,如袁宏所撰《东征赋》: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刘孝标注又记载了另外一种传闻:
《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4]
不管是与陶氏有关还是与桓氏有关,袁宏作《东征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现实环境(尤其是政治压力)对诗文创作的巨大影响。
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一作“望”,究竟是“见”,还是“望”,千百年来莫衷一是[5]。作“见”的话,文义稍胜一筹,但唐宋时代流行的文本可能确如苏东坡所说,以作“望”字为多,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唐陆曜《六逸图》卷[6],其中“陶潜葛巾漉酒”一图有陶渊明《饮酒》的诗句,正作“望”字。“见”“望”之争背后的历史真相很难还原,除了抄手的原因外,也有可能是陶渊明自己造成的差异。我们不妨作一个推测,陶渊明一开始用的是“望”字,已流传出去,后来改作了“见”字,也流传出去,结果造成两种文本都在世上流传。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有无“自定本”的问题。汉魏六朝时期,大部分文人作品以作家别集的形式流传,已有很强的“定本”意识,如曹植的儿子曹志回答晋武帝关于曹冏《六代论》是否为曹植所作的疑问时,说要回去查阅父亲的文集目录才能知道。这个文集目录,很可能就是曹植文集的自定本。当然作者的“自定本”后来也可能会遭到篡改,也就是“自定”之后又经“他定”,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序》: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7]
《赠白马王彪》的诗题,《文选》卷二四李善注云:“《集》曰:《于圈(鄄)城作》。”另外,诗题及诗序中的“白马王彪”,存在时间错误,因为黄初四年(223)曹彪的身份是吴王,黄初七年(226)才徙封白马,因此诗题和诗序一定是后来改的。顾农引《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说明,《曹植集》很可能经过明帝君臣之手的改定[8]。
有时还会出现两种“定本”(或版本)的情形,如《陶渊明集》就有南朝梁萧统所编的八卷本和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更极端的例子是整部著作(或其中一卷)的改写,如东晋孙盛迫于政治压力,其历史著作《晋阳秋》曾写两定本,寄于北方的慕容儁。《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9]
古代印度也有这样的例子,如12世纪史家、诗人迦尔诃纳的《王河》[10],因迫于皇权压力曾改写其中的第8卷,留下两种差异甚大的传本。学者云:“这一卷共有两个版本的亚原本……最初版本很不讨当朝国王喜欢:迦尔诃那(纳)的父亲被解除了大臣职务,因而迦尔诃那对当朝没有好感。然而,当《王河》被下令提交给朝廷过目,迦尔诃那重写了卷八的大部分章节,让国王显得更可亲。”[11]
(二)其次是抄录者和编纂者的原因,如《文选》卷五六班固《封燕然山铭并序》记载窦宪北伐的军队共有“骁骑十万”,《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所录《封燕然山铭并序》作“三万”,一个字差了七万人。如《文选》卷九班昭《东征赋》首二句“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其中“永初”(东汉安帝年号)当作“永元”(东汉和帝年号,永元七年为公元95年)[12]。又如《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或开关以延敌,競遁逃以奔窜”二句,李善注云:“言其利也。《过秦论》曰:诸侯以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也。”而贾谊《新书·过秦上》云:“(诸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13]《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亦云:“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颜师古注曰:“遁巡,谓疑惧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潘岳《西征赋》云‘遁逃以奔窜’,斯亦误矣。”回头来看李善注所引《过秦论》“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一句中的“遁逃”,显然是“遁(逡)巡”之讹,但潘岳《西征赋》很可能如颜师古所说,原文就作“遁逃”。
李善注本《文选》卷二六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乱流趋正绝”一句,颇难索解,而五臣注本《文选》作“乱流趋孤屿”[14],与下句“孤屿媚中川”形成顶针,意思豁然开朗。“正绝”二字,当是误由注文阑入正文,《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可以想见,注家对“乱”的解释“正绝”云云被误认作了正文。又《文选》卷二五卢子谅(卢谌)《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共更飞狐厄。”讲到两人共同经历的磨难,其中“俱涉晋昌艰”一句,与诗人当时的历史、地理状况完全不符,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条提出“晋昌”当为“晋阳”音近传写之误,很有说服力[15]。
六朝隋唐之间书籍以写本流传,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本《文选》、敦煌本佛经写卷等,与传世本有不少差异,多是抄手或抄本(抄手所抄之底本)造成的。如《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其一》:“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其中“达人贵自我”一句,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作“达人遗自我”,从诗义比较来看,谢灵运在这儿用了“杨朱贵己”的思想,显然作“贵”字胜[16]。像这样因字形相近而误者不一而足,东汉文人张升之误为张叔也是一例。张升字彦真,东汉晚期重要文人,所著文章有60篇之多[17]。后人又有称张升为张叔者,陆机《遂志赋并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18]陆机《序》中诸人皆称名,此处“叔”字当作“升”,盖“升”“叔”二字形近而讹。
许多类书所引的诗文也属于此类情形,如班固《汉颂论功歌诗》之《灵芝歌》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与《初学记》卷一五,《灵芝歌》云: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19]
其中“延寿命兮光此都”一句中的“此都”,《太平御览》作“此都”,《初学记》作“北都”,当系讹误。考《灵芝歌》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歌颂“芝草生殿前”而作,诗意与西汉《郊祀歌十九章》里的《齐(斋)房十三》非常接近。《齐房诗》曰:“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20]《齐房诗》为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芝生甘泉齐房而作,与《灵芝歌》所咏之事正复相类。班固《灵芝歌》中的“延寿命兮光此都”显是袭彼而来,盖“光”意谓光临,与“回复”之意略同,“此都”是指洛阳宫。
王国维在《〈乐庵写书图〉序》中写道:“余昔览元、明以来写本书,时时得佳处,而舛误夺落,乃比坊肆劣刻为甚。既而见六朝、唐人所写书,其佳处尤迥出诸刊本,而舛误夺落,则与元、明以来写本无异。盖古代写本多出书手,其为学士大夫手钞如郑灼之《礼记义疏》者,百不一见也。”[21]“古代写本多出书手”,是符合中古社会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22],而异文的多少,自然与抄手的学问水平高低、抄写认真与否有很大关系。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曾归纳“字体讹陋”的诸般情形:“有俗体之讹,有借用之讹,有妄减之讹,有妄增之讹,有分一字为二字而讹者,有合数字为一字而讹者,有因形近而讹者,有因音近而讹者。”[23]
二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
(一)篇题错误,如东汉初年杜笃《京师上巳篇》的误题。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收有杜笃《京师上巳篇》两句:“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并加有案语:“《书钞》原题杜季稚,稚殆雅之伪。又汉人七言率句句用韵,此艳、珠不叶,疑非出一章。”[24]其实,这首“七言诗”是杜笃《祓禊赋》中的句子,见于《艺文类聚》卷四,赋云:“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25]据赋文还可以校订“诗”中的两个误字:“胜”当作“媵”,“妃”当作“姝”。类似的例子还有《艺文类聚》卷六九引汉班固《竹扇诗》:“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此《竹扇诗》实为班固《竹扇赋》之讹,见于《古文苑》卷二[26],《竹扇诗》之五言四句乃从《竹扇赋》“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数句中来,又增加几个讹字。
又如崔骃《北征颂》,或题《武都赋》,或题《武赋》,皆误。今日本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七有“阙题”《颂》一首,罗国威整理该本时,注云:“此篇篇题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又不见于其他文献,故无从考稽。此卷中该篇排于东晋曹毗《伐蜀颂》之前,则可确定该文作者系晋或晋以前之人。”[27]笔者案,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四载崔骃《北征颂》,残存四句:“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扬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见于此篇“阙题”《颂》,惟“扬”作“杨”。据此,可定“阙题”《颂》的作者是崔骃,篇名当作《北征颂》或《窦将军北征颂》。
费振刚等整理《全汉赋》与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据《北堂书钞》收有崔骃《武都赋》残篇四句:“超天关兮横汉津,竭西玉兮徂北根。陵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元。”这四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字句略有不同,可互相发明。崔骃《北征颂》云:“超天关兮横汉津,朅西岳兮徂北垠。□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原。”“朅”意谓离去、离开,“北垠”指极北之处,《北征颂》“朅西岳兮徂北垠”一句显然胜于“竭西玉兮徂北根”,“□句注兮厉楼烦”一句中的阙字可据“陵句注兮厉楼烦”补“陵”字。“陵句注”二句中的“句注、楼烦、云中”都是地名,“句注”为古九塞之一,在今山西代县北;“楼烦”,古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云中”,秦郡名,治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显然也是地名,为秦郡之一,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征颂》的“九原”在文意上显然胜于《武都赋》的“九元”。崔骃又有《武赋》,残存一句:“假皇天兮简帝心。”见《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文》李善注,亦收入《全汉赋》与《全汉赋评注》。此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假皇天兮简帝心,爰比题兮获鼎宝。”可见,今存崔骃《武都赋》《武赋》两篇作品,均为后人误题,皆当归入《北征颂》中。
(二)序文问题,主要是传抄所造成的“张冠李戴”。一些序文的语气和用词显然不是原貌,如邹阳《酒赋序》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为《酒赋》。其词曰:……”[28]序文中出现的梁孝王是梁王刘武的谥号,显然不当出于邹阳之手。又如《北堂书钞》卷一二三所载班固“《幽通赋序》”,实际是前人(项岱)《幽通赋注》中的文字[29]。再如《艺文类聚》卷六一所载张衡《西京赋序》:“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这段话不见于《文选》卷二《西京赋》,未必为张衡所作,但《艺文类聚》为初唐人欧阳询所编,应有所本,庾信《哀江南赋》“陆士衡闻而抚掌,张平子见而陋之”两句,就用了其中的典故。从《〈幽通赋〉序》的例子来看,很有可能这篇《〈西京赋〉序》本是唐前单行《西京赋》篇题下旧注之文字,却被误认(或误抄)为序文。
还有完全的错植,如《太平御览》卷九一六所收张衡《鸿赋序》:“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已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粺,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这篇序其实是隋卢思道《孤鸿赋并序》中的文字,《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载:
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勿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云。其词曰……[30]
不难发现,所谓张衡的《鸿赋序》来自卢思道《孤鸿赋序》。大概是《太平御览》的编者看到《孤鸿赋序》中“平子赋曰”等字眼,便认为下面的文字全部来自张衡,而且还为它们加了《鸿赋》的标题。其实,张衡根本没有作过《鸿赋》,《孤鸿赋序》所引“平子赋”的“南寓衡阳”,来自张衡的《西京赋》:“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鶤。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不过是卢思道将“翔”字引作了“寓”。有意思的是,与魏征《隋书》同时的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卢思道传》则引作“翔”字,这可能是李延寿熟读张衡辞赋而作的个人改动。
(三)篇章错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班固所作的《北征颂》。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北伐匈奴还师,班固作《窦将军北征颂》,歌颂窦宪之武功。严可均曾据《古文苑》《艺文类聚》所载班《颂》残篇,将其辑入《全后汉文》,然篇章错乱非常严重,多处难以卒读。钱锺书云:“篇末‘荡残风’至‘四行分任’一节,文字讹脱,不可句读。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谓朱启连为句读之,以‘风’、‘阴’、‘淋’、‘弄’、‘任’为韵,亦未词达理顺。”[31]幸运的是,在元明时人所编的文学总集元陈仁子《文选补遗》及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均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里,可以看到班固《北征颂》的完篇。其中,《文章辨体汇选》之《北征颂》似从《文选补遗》抄来,但其本有优于《文选补遗》之处。
探讨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隋代牛弘所说的古今图书“五厄”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32]。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官方藏书的质量有很强的信心和很高的期待,而董卓之乱、永嘉之乱、西魏平江陵、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唐末战乱等几次大的战乱,对文献造成了巨大破坏。官方“定本”(一些别集、总集或许本来就没有“定本”)既已不完,唐宋时代的整理者又甚荒疏,就造成了中古文献的混乱状况。
在六朝别集、总集大量散佚以后,文本歧异、莫衷一是的情况在两个时期特别突出。一是唐代初年,如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不够严谨,常常有混淆作者、张冠李戴的情况。林晓光曾以《艺文类聚》为个案,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唐宋类书对六朝文献的载录,并非全文照录,甚至也不是局部节录,而是进行剪切删削,再将零碎片段予以拼接,其形态更应称之为截取缩写。”[33]这种情况不仅在《艺文类聚》中存在,在《北堂书钞》(成书于隋代)、《初学记》等其它早期类书中普遍存在着。今天的人们可以借助于一些六朝隋唐文献的旧抄本,如敦煌吐鲁番所出唐抄本《文选》、日本藏唐抄本《文选》、《文馆词林》等[34],来纠正传世本的一些错误(当然也要注意到这些唐抄本本身也有一些文字错误)。二是北宋初年,问题集中于《文苑英华》《古文苑》等诗文总集上。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中的萧梁诗文,与其它传世文献相较有不少歧异。
三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歧说”
“歧说”更为复杂,涉及别集、总集、史书、类书等各种文献。“歧说”出现的原因,既有后人故意作伪的情况,也有文本传播的因素:
(一)真伪。如《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历代学者意见不一。顾炎武《日知录》举出五条证据,论证其非汉武帝时代所作。逯钦立《汉诗别录》[35]、伏俊琏《〈柏梁台诗〉再考证》[36]、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37]等文,则认为《柏梁台诗》作于汉武帝时期,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又如关于“苏李诗”[38]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讨论,至今没有一致意见。
再如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39],其质疑不无道理,因为如果《赠答诗》确是秦嘉、徐淑夫妇所作,以他们二人的创作水平,却没有被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和《后汉书·列女传》收入,终究是一件奇怪的事。又如署名蔡琰的《悲愤诗》(五言和七言两首,见范晔《后汉书》卷八四《列女·董祀妻传》)、《胡笳十八拍》(琴曲歌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40],有学者从《悲愤诗》首句“汉季失权柄”看出了伪作的狐狸尾巴。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孔雀东南飞》,序文中出现了“汉末建安中”的字眼,也让人怀疑[41]。
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学者对此文真伪存有疑问,“一般认为此檄乃荀彧死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征吴之际为荀彧从子荀攸而作,或齐梁时代文士的伪作,详清人朱珔《文选集释》卷二一、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六、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七年(212)” [42]。顾农认为:“从内容来看,此文应当不伪,只是开头打着尚书令荀彧的旗号是不对的,此公已死于建安十七年(212)。估计此文在流传过程中有被浅人妄改的地方。”[43]
(二)篇题。如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见《文选》卷二七(《乐府诗集》卷四二《相和歌辞·楚调曲》同),南朝梁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作《怨诗》,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称《团扇》诗。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研究者对其篇题提出了疑问,见曹道衡、沈玉成关于此文的讨论[44]。《文选》卷二七鲍照《还都道中作》,李善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浔阳还都道中》”注云:“此诗《文选》题为《还都道中》,毛扆校宋本《鲍集》作《浔阳还都道中》,皆无‘上’字,则‘上’字为误衍。此诗盖即作于发浔阳时。”[45]其实细细思来,诗题“上浔阳”也可以说得通,因浔阳地处江州,对都城建康来说处于上游,诗人先由建康溯流而上,后复还都,诗题将“上浔阳”与“还都”二事合并言之,理解上并无窒碍。
(三)作者。如《初学记》卷一九西汉王褒《责须髯奴辞》,《古文苑》卷一七以为东汉黄香作。又如东汉《征士法高卿碑》实非胡广撰,《太尉刘宽碑》非桓麟作,《艺文类聚》所系皆误。胡广《征士法高卿碑》载于《艺文类聚》卷三七,考法真卒于中平五年(188),年八十九,而胡广卒于熹平元年(172),年八十二,卒年在法真前,不及为法真撰碑[46]。此碑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法真传》载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这段话正好可以与碑相印证,碑云:“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范晔《后汉书》所引郭正的话盖简括碑文而成。
《太尉刘宽碑》有两篇,一篇为蔡邕作。另一篇载《隶释》卷一一,又略见《艺文类聚》卷四六,云后汉桓麟撰,严可均从之,将其辑入《全后汉文》卷二七。然此碑实非桓麟作。据《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桓麟在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年纪至少15岁,且其早卒(年四十一),如以建和元年(147)为桓帝初,则其卒年当在灵帝熹平二年(173)左右。据《太尉刘宽碑》,宽卒于中平二年(185)二月,此时桓麟已去世多年,不可能为刘宽撰碑。该碑字句多同于蔡邕《太尉刘宽碑》(载《全后汉文》卷七七),颇疑亦出邕手[47]。
另外,东汉时代出现的众多官箴作品,也存在着作者淆乱的问题,详见下页表。
又如南朝梁陈时期陈昭的《昭君怨》(见《艺文类聚》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和《阴铿集》将著作权给了阴铿,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两收之。[52]有些诗歌的作者问题又与代笔有关,如《玉台新咏》有《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题魏文帝曹丕作;而同一首诗列入《艺文类聚》时,则题为《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署徐幹作。顾农认为:“考虑到徐幹在曹丕那里当过‘文学’,侍从之臣代主人作诗非常常见而很少有相反的情形,我们宁可相信晚出的《艺文类聚》。”[53]
(四)作者与篇题都有问题。如《文选》卷四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李善注云:“《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可知这封书信的作者和收信人有两种说法,一是赵至与嵇蕃,二是吕安与嵇康,李善把二说原委都罗列了出来,但没有作出判断,后代学者多以后说为是。
余 论
上述情况虽然多是一些小问题,却影响到我们对中古文学史真相的认识[54]。正如前人所说,“校文字易,校是非难”,而乱篇之整理、歧说之鉴别更是不易。对于汉魏六朝诗文中存在的这些文本流动和变异现象,要求我们跳出具体作家、作品的束缚,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状况。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文字异同(“异文”),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如“乱篇”“歧说”);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中古诗文文本一些貌似无序的现象并非无序,而是无序之中的“有序”,如“赠答诗”的收录问题。六朝时代两个作者之间的“赠答诗”,常常是“赠诗”与“答诗”一同完整地被收入各自的文集,这种现象在陆机、陆云的别集中普遍存在着。因为不收入的话,读者很难孤立地来理解文本,正如后代诗人的原作与他人的和诗都同时被收录文集之中,一个文本必须在一个文本群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先秦两汉的子书不少需要以篇章为单位来讨论[55],汉魏六朝文学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工作,一些诗文的篇题、序文、正文需分开讨论,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篇题问题,如前面讨论的崔骃《北征颂》的问题。序文的情况也很复杂,除了前面讲过的例子,还有序文后加的情形,如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诗序。据陶渊明所言,这篇序文是在诗歌完成以后才写的,诗歌写作与序文写作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蔡邕的《述行赋》更为复杂,其序文与赋的写作时间不一致,当是后来补作。桓帝延熹二年(159)秋,梁冀新诛,宦官头目徐璜、左悺听说蔡邕善于鼓琴,便以天子的名义命蔡邕赴京。蔡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述行赋》就作于此时。但在《述行赋序》里,蔡邕直斥“五侯”之逆行,并讲到桓帝对直言极谏之士的残酷打击: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宦官之祸,触怒桓帝,被处以极刑;大鸿胪陈蕃也因求情被桓帝下狱,后免归田里。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延熹三年(160),《述行赋序》很有可能是蔡邕后来的补作[56]。
抄写带来的文本变动以及文献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在西方也很普遍,其成果有可资借鉴之处。如关于《圣经》古代写本的研究表明,《圣经》的诸多异文和文字差异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他们有时会看错和听错单词,从而产生字母的拼写错误;有时会无意中漏掉短语和句子;有时会改动(或纠正或希望改进等等)自己所抄的文本——抄写不一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常常伴随着对文本有意的改动[57]。除了西方的古代写本研究,印度古代经典以及梵文写本的研究,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例如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间印度著名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流传至今,存在许多文字差异,很多属于诸说并通的情形。
注释
[1]关于写本、抄本等概念的辨析及比较,参见张宗品《写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童岭《“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台湾《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第257—280页。
[2]严格说来,“歧说”不属于简单的文本歧异,但为了全面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流动与变异的复杂性,笔者在这儿一并讨论。
[3][4]《世说新语笺疏》,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第270页,第27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据袁行霈统计,陶集异文有740余处。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载袁著《陶渊明研究》,第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袁行霈:《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第5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7]萧统:《文选》,李善注引,胡克家考异,第340页、第915页,清胡克家刻本《文选》,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本文所引《文选》及李善注,如无特殊说明,均见此本,下文不一一出注。
[8]顾农:《曹植札记二题》,《书品》2013年第2期。
[9]房玄龄等:《晋书》,第214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王河》是一部以诗歌形式记述克什米尔王朝历史的著作,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古代印度现存最早且唯一的史书。
[11]迈克尔·维茨尔(Michael Witzel):《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文献学——以印度学为重心的回顾》,张远译,《古今论衡》第26期(2014年6月),第139页。
[12]参见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一二引阮元的考证,梁章钜:《文选旁证》,穆克宏点校,第301—30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锺夏校注,第1—2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萧统:《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吕延济等注,第409页(下),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15]何焯:《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第9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参见傅刚《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发覆》,《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后收入傅《〈文选〉版本研究》,第276—2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第2627—262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8]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册,汪绍楹校,第4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隐)》,第201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9]徐坚等:《初学记》下册,第37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李昉等:《太平御览》第3册,第2578页(上),中华书局1960年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版。
[20]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06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167页,线装书局2009年版。
[22]中古社会书手之多,如《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载南朝梁武帝时代所编类书《华林遍略》传到北齐境内的情形。李百药:《北齐书》,第515页,中华书局1972版。
[23]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
[2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第165页、第10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6]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岱南阁丛书”重刻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九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27]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1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28]参见《西京杂记》(葛洪:《西京杂记》,第178—18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及《初学记》(徐坚等:《初学记》,第24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9]参见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汉班固〈幽通赋〉并注校录考证》一文的考证,见载许云和《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0]魏徵等:《隋书》,第1398—1399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31]钱锺书:《管锥编》,第1572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32]“五厄”之说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33]林晓光:《〈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原——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34]参见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5]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10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伏俊琏:《〈柏梁台诗〉再考证》,《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三辑,第331页,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7]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38]李少卿《与苏武三首》、苏子卿《诗四首》,见《文选》卷二九。又《古文苑》载十首,苏武二首、李陵八首。
[39]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0]参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较近的研究有王小盾《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胡笳十八拍〉和琴歌》,《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
[41]关于以上诸名篇真伪的学术史讨论,参见刘跃进著《中古文学文献学》相关章节的评述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2]冈村繁:《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罗国威译,载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第123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
[43][53]顾农:《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第95页,第113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44]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58—59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关于此文敦煌本及文字异同,参见冈村繁著、罗国威译《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载罗国威著《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第88—123页。
[45]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五,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6]见《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法真传》、卷四四《胡广传》,范晔:《后汉书》,第2774页、第15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47]陆侃如也有同样的意见,但未加以论证。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48]《全汉文》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有详考参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21页(上)。
[49]《司空箴》,《艺文类聚》卷四七作扬雄,《初学记》卷一一作崔骃,《古文苑》作扬雄,注云:一作崔骃。《全汉文》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文选·西都赋》注引首二句作扬雄。”《尚书箴》,《艺文类聚》卷四八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注云:一作扬雄;《太常箴》,《艺文类聚》卷四九作扬雄,《初学记》卷一二作崔骃,《古文苑》作崔骃,注云:一作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卷四六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
[50]《全后汉文》卷四四严可均案语云:“《司空箴》,《艺文类聚》四七以为扬雄作……《尚书箴》,《初学记》十一以为繁钦作……《太常箴》,《艺文类聚》四九以为扬雄,《古文苑》作崔骃,注云:‘一作扬雄。’……《大理箴》,《初学记》十二引汉崔德正《大理箴》,未详德正为谁。《古文苑》作崔骃,今据之。……《河南尹箴》,又《御览》二百五十二作扬雄,误。西汉无河南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15页。
[51]《侍中箴》当为繁钦作。
[52]参见刘国珺《对古籍中阴铿、陈昭的昭君诗考辨》,《南开学报》1988年第3期;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680—681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5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复杂性,以便读者在阅读时予以足够的注意,并无意否定固有的以《文选》为基础的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稳定性”。
[55]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第93—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6]这种文本形成过程中作者自己的补作和回改,属于创作问题而非传播造成的,蔡邕《述行赋序》、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中存在的“年代错误”,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57]参见Michael D. Coogan ed.,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the Apocrypha, Augmented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extual Criticism”, p.461。
来源: 《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