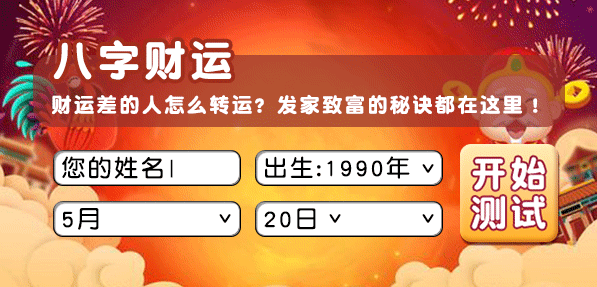八字无官能发财吗(八字无官能发财吗女命)

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2),小京官也能发大财
本文来自:《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宗承灏著.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7
“京”字招牌升得快我们都知道,资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机关干部的资历很多时候是靠一杯茶、一张报纸泡出来的,与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官还是碌碌无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在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
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某位京官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作为官员来说,个人的仕途命运,抛去个人因素之外,很多时候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大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所谓的古代官僚制度,制度里的那些法律条文对官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层面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不被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并且约定俗成地成为官场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京官们的升迁。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
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待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五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
“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
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
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
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
像内阁中书这样职卑位尊的京官打着一个“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实权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
“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州县数以千计,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知县的顶头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级之间相差有三四级之多,这三四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知县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个知县想要直升为像知府这样的正印官,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
位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全景)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还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地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优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员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泥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
就官僚制度而言,那些身处不同衙门里的官员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升迁际遇。凡是经过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升迁资格的候补官员都要到吏部听候铨选。吏、礼二部的司员,除了进士可以授主事、参加国家特考的贡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贡生和监生花钱捐纳人官。
另外吏部在掣签选官的时候,也不得将吏、礼二部纳人其中。
这里所谓的掣签选官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创立的选官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打乱后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选用官员,皆由选人自掣,有点撞大运的成分。清朝沿用此制,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
在官员选用上,户、兵、刑、工四部与吏、礼二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其余四部虽然比不上吏、礼二部进步得快,但在京官这个群体中也属于佼佼者。不要说部与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职也会分个三六九等和好坏优劣。
作为京官,最应该修炼的本领是熬资历。熬的是时间,熬的是资格,能够熬出头的就可能成为大京官或者地方大员,但是大多数人在这条路上耗尽一生,也难以有所作为。
比如说清朝京官中的侍郎就是在六部熬资历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都是先从工部起步,然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但在京官的圈子里却被视之为“升任”。
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虽然手里握有工程项目和工程款项,可与其他几个部门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兵部掌管着天下的兵马,战时多事,和平时期又无事可做;刑部掌管着司法刑狱,因为刑部官员拥有合法伤害权,所以也就拥有了为自己造福的权力;礼部掌管的是意识形态,负责文教,本应是清水衙门,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负责科举考试,所有想要进入官场的读书人都无法避免地要和礼部打交道;户部就更不用说了,户部又称为“富部”,他们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和开支,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能够卡住命脉的人往往处于权力的核心阶层,另外官家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户部真金白银的支持。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把持着官员进退升降的大权,这是官僚集团最为在意、也最为敏感的权力。
根据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路径,我们可以按照六部实际权力从小到大将其排列出来:工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吏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最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进入的可能。由此可见,同级官僚不同权,更不同命。
在京官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士身份的京官,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曾经供职于这些衙门的工作经历,通过科举考试来取得进士功名,然后获得跻身于更高权力地位的资格。为了不当一辈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远,
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在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绩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与他们小京官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京官都是从各省国子监的生员选的尖子生,礼部官员登记造册后奏请皇帝。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会考于保和殿,称为朝考。通过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门谋个实职。
选拔者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名士,早已进入国家的人才贮备(登朝籍)。他们参加进士考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殿试读卷的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本来就是“老相识,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年-1904年)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显位,主要是由于六部司员都可以通过掏钱捐纳取得,录用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正规。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其结果就是让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变成破铜烂铁。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经处于无法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愈陷愈深。
小京官也能发大财京官穷得口袋里叮当响,这好像成了古代官场上达成的统一共识。但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其实这种京官的穷是相对而言的,那些占据权力要害位置的京官就是他们哭穷,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眼泪。有人习惯用收入来衡量权力的大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权力能够为官员带来收入。
一个官员的收人越高,表明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其实这只能是个推理,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决定官员收人多少的要素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永恒的变量。
我们就拿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知县甲和知县乙,虽然同为知县,可他们权力所辖的区域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知县甲和知县乙动用权力所能够获取的灰色收入也就存在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知县甲和知县乙的个人修为也决定着他们的贪廉程度。如果知县甲立志要做一个海瑞那样的清官,就是把他放在应天巡抚(省长)的位置上,他的灰色收入也远远不如一个知县(区长)。综合以上因素,官员的收入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权力的大小。
但是对于京官来说,情况与地方官员又有所区别。首先在决定其收人的各种要素中,存在的变量有所减少。这样一来,京官的收入多少与权力大小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权力值就约等于个人收入。
官员所拥有的公权力所圈出的区域越大,那么他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多。真正穷的,只是那些清水衙门里的小京官。这帮小京官是一群被称为“京曹”的人,他们仅仅是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权力不大,工作也很清闲,他们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一个在底层刮油水的胥吏。
对于一名低级别的官员,既没有来自下级的孝敬,又没有实实在在的公务经手,想要过上富足的生活是非常难的。胥吏的收入与所在的岗位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盘踞权力要害位置,他们就可以揩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更为明显。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就拿“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来说,换算成今天的钱粮,相当于一年两万多块钱。要知道,当时可没有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几口人吧。如果仅靠着台面上的两万多块钱,京官的日子几乎没法过下去。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京官的“穷”与京城老百姓的“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老百姓的“穷”是穷在温饱问题上面,而京官的“穷”则是消费结构性的穷。京官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他的那些同僚们和各级官员。作为官员,他们所要求的生活标准绝不仅仅是达到温饱线。他们既要追求酒足饭饱的物质生活,还要追求声色风雅的精神追求。而满足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需要的是真金白银。
京官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刮地皮。比如说,一个在六部供职的主事(文吏),级别属于七品官。地方上的七品官担任的是知县,一个知县不贪不抢,一年正常的收人也有几万两银子。可七品官放到京城里,就是权力系统内的最底层,他们的合法收人(工资)是四十五两银子,顶多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由此可见,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是有办法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官员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员,刮来刮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权力资源,他们的权力资源就是位居权力系统的中枢部位。这个部位拥有合法伤害地方官员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权力伤害,地方官就要向京官馈赠别敬、冰敬、炭敬等各种名目的灰色收人,其实这是官家权力收益的二次分配。
地方官员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需要一次分肥,官员既是受贿者又是行贿者,由此引发了官员权力资源的二次分配。
位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大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长)。在赴任之前,他觐见了当时的咸丰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类似于今天的组织谈话。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他还要履行官场应该遵守的灰色章程。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一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别敬),京城各大小部门里的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
当时新官赴任前用于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传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开列出了标准。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等于是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不可小觑。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
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关系。与人品,与感情,与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它只是官场的“灰色章程”,是一种权力寻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游戏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到圈外面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
作为一个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上赴任的消息后不是一家人喝庆功酒,而是一家人想办法先四处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张集馨日后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还不起。
我们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清朝道咸年间的工资标准,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佣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人,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人,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人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搜括民脂民膏的任务就很重。
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这里有两个例子:当时的陕甘总督(一把手)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有两种:
一是借鸡生蛋。也就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拨出上万两的银子,然后想办法将银子借给典当行,自己坐收利息。
二是预支生钱。也就是官员即将离任的时候,将所辖之地的税赋打折,鼓励粮农预支来年的税赋,这也称为放炮。有时候,即使官员没有离任,也会放出假消息,催着乡民们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成了养活权力集团的血液。
张集馨曾经担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实际上向民众征收的粮食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一万石余下来的军粮,自然就成为陕西粮道的囊中之物。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官场上有句老话:“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话说得很形象。按照官家权力的正常关系,权力的等级序列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官大一级,自然是权大一级;权大一级,自然在权力系统中的造福和伤害能力也就比别人(下属)大一级。人本来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中国古代官员对此更是异常敏感。官家权力系统除了这种纵向上“绝对服从”的关系之外,还有横向上“分工不同”的关系。也就是在一个权力大系统内,依据不同的职责分工而产生权力小系统。
就拿明清时期来说,地方设藩司衙门,长官为布政使(分管财税的副省长);同时设臬司衙门,长官为按察使(省高级法院院长),布政使无权干涉按察使审案,按察使也无权插手地方的钱粮事务。但依权力的层级原则,布政使与按察使均受巡抚(省长)节制。巡抚和布政使虽然是同级别的官员,但是布政使要受巡抚的节制;按察使比巡抚官小一极,可以说巡抚是他的上级。
这种纵向上分层,横向上分界的权力结构是理论范畴内的权力运作方式,但是这种运作方式常常会在现实中碰壁。很多时候,那些居于权力等级上层的长官反而会受制于权力等级下端的小吏,为了摆平某件事,他们往往需要低眉顺眼向小吏行贿。
有一个京城小官吏啃噬地方高官的典型案例。
清朝同治年间,由天平天国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即将走到尾声,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进人全面扫尾阶段,庞大的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挽救帝国于危难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功不可没。按道理说,就算朝廷不重奖,报销军费也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让曾、李二人想不到的是,手续齐全的军费报销居然会卡住。卡住他们的不是皇亲贵戚,也不是比他们高一级的京官,而是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官场小人物,级别都大多是七品的户部文吏(办事员)。
我们都知道在食物链上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之说,可虾米吃什么呢?有人说是淤泥,但我要告诉你,浮游在水面上的虾米反过来也是可以吃大鱼的。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中央六部各衙门的胥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上大鱼,关键不在其身份高低,而在于他手中有多大的权力。
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是轮不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向各地方官员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而在这六部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户部因为是管报销的,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有灰色地带的存在。
对于那些不谙熟规则的人,往往都办不成事。就像这眼下的军费报销,报销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二位可以说是晚清权力集团的两位大佬级人物,可他们照样要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
要想报销款尽快到位,如果当事人装傻,不给当事的户部书办“意思意思”,来回折腾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意思意思”的标准主要还是按照报销总额的比例抽取,总额越高,抽取的那部分也就越多。军费开支应该是报销款项中数额最为庞大的项目之一,那么作为户部的经办人相应得到的收益也应该是丰厚的。比如你要报销一百万,起码也要拿出五万到十万来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还有发饷、拨款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你的礼没有送到,我就拖着不给办,看是你急还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也不怕担责任。当然这笔钱胥吏是不可能独吞的,权力集团的分肥绝不是让一个人吃饱,其他人饿死。这笔灰色收入,司官、堂官也是见者有份,但捞到大油水的还是具体经办人员。所以清代户部的大小官员、胥吏是六部之中最肥的缺,甚至有人称,户部书吏的富裕程度,并不输给京城里的那些王爷们。《清稗类钞》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因为户部的胥吏大多数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是当时北京城内的高档住宅区,而司官则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比自己的下级差了好几个档次呢。
吏部、兵部就趁那些官吏升迁、补缺之际大捞一笔,比如说,如果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人知道信息后,必须马上到吏部或兵部上下打点行贿。书吏根据这个空缺位置带来的利润空间来索贿,真正按照资历和能力安排职位的少之又少。至于工部、礼部、刑部相比之下就是清水衙门了,他们只好等待像国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时再狠狠地捞上一把。
这一次,虾米要吃定大鱼,小吏要教教封疆大吏怎么做人。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将当时的报销过程转录如下:
一是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然后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
二是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
三是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
四是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
五是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尘埃落定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以上报销流程我们可以看出,报销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关键还在于户部的审计那一关,其他环节基本上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但是体现户部真正权力的除了审计,就是“批驳”。
如果户部文吏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合规定,说你有做假账的嫌疑,那么你的报销就要搁置。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所在,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和借口,而且理由是正式权力范畴内的,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能够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叫做“部费”。这笔经费专门用于“跑部钱进”,打通上下环节。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非常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烦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也就是说,财务工作是一件让人头疼万分的事,不熟悉这项工作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所以说,那些书吏如果要挑报销者的财务问题,对方也是一头雾水,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也有。
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就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作为一名合格的户部书吏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知识,而且还需具备过人的精力,因为审核的过程也非常耗神费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们去做。也就是说具体办事人员在具体操作这个事情,分管工作的官员只等着利益分配,坐享其成。
按照当时的权力结构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儿,类似于我们今天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他们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
问题是,管归管,可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意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消磨时间,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做文章。对于办公室这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死读书、读死书的脑袋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就转移到了书吏手中: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
在正式规定中,书吏则是一些没有地位的人,类似于政府聘用的不在编人员,按规定五年一续聘,不能连任。他们不仅连正式的工资都没有,甚至连一点伙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买。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有两百多个。书吏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他们办事的书吏来负责。
当然对于书吏们来说,他们工作的动力与领不领政府的薪水无关。他们有财务审计的权力,就看你送不送钱,这些地方官员用来活动的钱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
户部书吏因为手中有了这种权力,导致各级官员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账目。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以曾、李二人当时的地位,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普通官员并无二致,也就是花钱、找人、托关系。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这个人是湖北省的一个道台,曾经在户部任过职,在部里也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王文韶对户部文吏这一套办事章程并不感到陌生,他先是托人去找具体办事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的胃口很大,要求得到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加起来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八千万元。
曾国藩所托之人是李宗羲,此人是江宁(南京)布政使(江苏省长)。其实李宗羲并不熟悉户部的人,他转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和户部的书吏做了私下沟通。经过私下里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八万两。尽管书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曾国藩还是不满意。即便只掏出八万两,筹措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因为这笔钱是不可能通过正式权力确定的财政制度到手的。于是,曾国藩又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能够免于审计。皇帝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就同意了。但为了不得罪人,曾国藩在向皇帝打报告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在前面和户部的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漫天要价,不然真就太为难了。
“灰色收入”必须有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们就拿翰林来说事,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一方面可以得到时下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这两方面可以使得自己获得官场升迁的资格。
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地位显赫自不必说。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收入却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时人常有“穷翰林”之谓。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就将京官的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实行的是例支双俸。就是说,每个月为京官开双份工资。这样七品京官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两。另外再发一些粮食,“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22.5石)“禄米”。钱和粮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当时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换算,他们的收入也不过就是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些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二万五千多块钱。
作为一个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话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也不难找到佐证。
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在日记里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当时也有翰林做诗来哭穷:
“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
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
唯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脸,走路上班,还要迈八字步摆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坏了跟在后面有急事要办的主,只有在心里诅咒他们。
其实“低薪制”对于官员们来说只是绣花枕头,中看并不中用。虽然打着为朝廷节约开支的旗号,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伤害到的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很多清官们买不起房,住在京城外围的“棚户区”,一个个面有菜色。
对于那些贪婪的食权者而言,“低薪制”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搜刮灰色收入的充分借口。朝廷俸禄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话就连皇帝听了,也觉得有七分道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此使得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可以原谅的行为。
当然像翰林院这样清水衙门里的京官是个特例,因为他们手里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那么,通过权力来获取灰色收入的基本条件也有限。但是为了能够在这条食物链上存活下去,京官们也会学着在铜墙铁壁的权力丛林里四处打洞找出路。有想法总会有办法,许多京官的智慧还是无穷的,他们能够从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里发现有机可乘。
清代中后期,京官通过替外官(地方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能够搭上地方这条权力管道,无异于从权力结构的上层插下了一根隐形的供血管道。很多人靠着地方的供给,也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虽然在他们的诗文里和抱怨里还是在不停地哭穷,可不知不觉哭出了“幸福的味道”。
小京官们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的同时,朝廷往往也在有意无意地为他们解决生计之困。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那就是“得差”,不过将其改为“得钱”更为恰当。就是将翰林们下派到地方上办理公务,在办公务的过程中,这些离开京城的翰林们才算真正得到权力的滋润。虽然他们在京城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到了地方却是皇命在身之人。
那些地方官员对大京城来的“小角色”丝毫不敢怠慢,就算不求他们回去后为自己美言几句,也要避免他们回到京城之后对自己的祸害。京官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次出公差的机会,可以发一笔横财,何乐而不为。况且这笔横财还不是小数目。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
朝廷下派翰林们的差使大多是乡试主考。国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主考官的灰色收入也是因地而异,标准不一。比如说,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各省路费标准: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嗣后乾隆六年又规定,户部每人先给二百两银子。
正如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就是说剩下的也无需缴还。而考官出行,都是由沿途的驿站付给夫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所以朝廷发的差旅费也基本上进了个人腰包。
乡试结束的时候,地方官场按照规则还会送给主考官员一笔价值不菲的“辛苦费”。这笔收入,对于一个穷翰林来说,无异于买彩票中了一次大奖,往往会使他们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为表敬意所送的礼品)等灰色收入。另外作为主考官,衔皇命选才,既是一种荣誉,又可以成为这些举人的“座师”,也就是说翰林是赚大发了,不光有钱收,而且还能收获官场上的潜在人脉,可谓一举多得。
清朝光绪年间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曾经在他所著的官场日记《越缦堂日记》里,对自己的京官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构。李慈铭当时在户部任郎中,户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一个油水部门,被称为“富部”。能够在户部谋上一官半职,应该是京官们梦寐以求的事。
李慈铭所在的江南司是户部的第一司,也称“头司”,因为它主管着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李慈铭的郎中是个多大的官呢?应该说不算大,也不算小,正五品,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司的司长。
能在户部捞到一个司长当,应该说李慈铭在京城里混得也不算差。更为重要的一点,他所占的位子是令京官们羡慕的肥缺,权力能榨出油水。可就算身居肥缺,也挡不住李慈铭哭穷。
按照李慈铭的官场日记里记载,他一年的收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正俸、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还有书院的束修等工程项目。在日记里,李慈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收人情况:这一年他得到的工资收人是一百三十五两银子(俸银加上养廉银)和大约一千二百市斤(7.8石)的糙米。按照当时的京城米价大致是一石三两银子,如果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一百元钱。这样,一百三十五两银子就折算为一万三千五百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钱。而李慈铭一年的总收入高达2061.2两、米7.8石,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三十万元。李慈铭一年的工资收入和实际收入之比为1:15,两相比较着实令人震惊。
在李慈铭的灰色收人中,我们就拿馈赠和印结银来说,这两项灰色收人主要是指外官的赠送,这也是李慈铭灰色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换言之,如果官家制度能够有办法将这两个渠道堵死,在当时的低俸制下,京官们想要活得滋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可惜,官家制度在这里玩的却是故意一漏。堵不上,也堵不了。
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人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因为京官在死工资之外的灰色管道很有限,而外官们在地方上可以拥有吸纳灰色收人的各种权力管道,名目不一。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吹气球,掌握不好技巧,我们会将气吹向一端,使得局部膨胀,结果没等气球吹到最佳状态就爆掉了。如果我们掌握好技巧,将气吹得分布均匀,气球会吹得又大又圆。同样的道理,通过权力管道吸纳的灰色利益,不能只肥一端,这样就会使权力管道局部肥大造成堵塞,而不能自由流通。何况食权者都是在官僚体制里过日子,只肥局部,也不合规则。
如果说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贯通,那么权力所能够产生的灰色利益则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吸纳。外官需要在京城各部衙门建立关系网,所以他们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这种送礼的方式还有着听上去很不错的名字,夏天孝敬京官买冰消暑的钱称为“冰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称为“炭敬”、官员离别京城就任地方时的“分手礼”称为“别敬”。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的一部分,但是混迹官场之人,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受之坦然,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陋习之一。
保定 直隶总督署
即使那些生财无门的清贫官,逢年过节,也要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座师等人送上节日红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在张着欲望的大口等待送上门的馈赠,其中的清廉者也不是没有,不过太少。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计算,自己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之徒,也不是一个官迷。可他们总要为属下着想。古代做官,裸官者很少,基本上都是组团赴任。屁股后面跟着家丁、僮仆、跟班等等,他们大老远跟着你千里赴任,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为谋生计。还有那些鞍前马后为你服务的书吏、衙役、门子,他们也是为了能跟着你风风光光,狐假虎威捞油水。就算京官自己不要一分钱,你又怎能让人家一分不取?如果官员都去学了海瑞,他们也跟着吃不起肉,官员身边早就没有一个帮手了。
李慈铭在自己的官场日记里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能够扯上关系。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去攀附,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四百一十八两。
我们再来看一看印结银,这项费用又是从何而来?清代各省人士到京城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印的保结文书——印结。这个印结不是白拿的,而要花钱去买,所花的银子就是“印结银”。李慈铭在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达346.1两,算是比较多的一年。
李慈铭在这里吃的是灰色收入,也称为“陋规”。官场陋规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与对方级别无关。在李慈铭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除去那些在编不在岗的(候补京官),光是在职的京官就有近六千五百人。
李慈铭在当时是个正五品的郎中,在他上面还有四个品级,下面也同样有四个品级,而正五品刚好处于九品官制的中央地带。
洪振亚先生在他的《亚财政》一书里就以李慈铭为例子去推测京官集团在一年时间里所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按照李慈铭在光绪十三年里的收入来推测,剔除那些实物型礼物,也不算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特殊工程项目,只算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即团拜银)等项目的真金白银,这三项合起来就是962.1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太离谱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数字为基数,六千五百名在职京官收受的灰色收入竟达到六百四十万两白银。这可就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数目了。李慈铭一年二十万元(折合人民币)的收人的确使他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而事实上,他在日记里走了两个极端:一边在哇哇地哭穷,一边又在日记里炫耀着自己在京城里的幸福生活。
京官哭穷,难免会让人生出疑惑。要知道那些京官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其中“为赋新词强说愁”者不在少数,能够不抹辣椒水就哭出眼泪已经算是对得起观众了。这样的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做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做派,俸禄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
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两千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从其支出项目来看,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二百五十两银子,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其实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从李慈铭的账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样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乐性消费上。他用于馈赠上级等社会交往花费两百两;在外面消费时打点的小费(犒赏)一百两,与朋友饮宴花去一百六十两;到戏园子听戏(娱乐)消费六十两;购书花去两百两;包了一个二奶(买妾)花去一百八十两,还有其他消费三十两。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他对自己下的定论是,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按这种逻辑,如果交际圈子大,不知还要到何种程度。
本文来源:《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宗承灏著.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7
连岳:官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
#好内容我来评#
Claude Monet
连叔,你好,展信佳。
每天都看你的回信,也在别人的困惑里解决了很多自己的困惑,犹豫很久要不要给你写信,因为我觉得和多数人比,我的困扰并不能算做是困扰,甚至有点凡尔赛,但是确实是困惑我很久,自己也想不明白,希望你能指点一二。
先简单说下我的情况吧,90后,在三线省会城市国有企业工作,爱人是公务员,家里有房有车有一子(有房贷,但很少),现在在备孕二胎。说实话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希望的生活:工作稳定、压力小、离家近,也不太加班;夫妻和睦,爱人踏实、勤奋、有责任心;两家父母都感情和睦,明事理。现在的生活我是真的很满意、很幸福,觉得我的一生能这样稳步的过下去,我就很知足。
因为我所在的部门是单位的核心部门,所以我如果想向上奋斗更高的管理岗,我的确比别人有优势,所以周围的人(主要是父母和单位的领导)都希望我在工作上多付出些,去竞争管理岗。但是这对我真的没有吸引力,我太了解我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了,我心软,实在,脸皮薄,优柔寡断,抗压能力弱,在人情世故上一点都不通透甚至有点迟钝。这些弱点曾经给我造成很多困扰,而且我努力了很久才发现这是性格所致,无法通过我后天的努力改变。也是这两年我才想通,开始真正的接纳自己的弱点,开始觉得自己很好,开始觉得不需要变成别人也值得世间很多的美好。
我很清楚当领导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更大的责任,我的性格当不了好领导,而且我也不愿意改变现在生活的丝毫。我一直认为生活是多方面的,现在的我可以有富足的安全感,有充裕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照顾父母,有更多的精力支持爱人的工作,这些让我充满幸福感。可是一直以来总被教育要努力,要奋斗,要拼搏,要向上,好像人生成功的标准就是有钱和有权,我现在的生活没被算在内。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很矛盾,一边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美好,一边又怀疑这样安于现状是不是不好。可是在工作岗位上一辈子当好一颗螺丝钉也不容易啊,教养好一个孩子成为有用之才也不容易啊,照顾父母夫妻和睦家庭幸福也不容易啊,这些都需要智慧、需要时间、需要精力去经营,我选择想要一辈子都过现在的生活就是胸无大志吗?
说的有点乱,想问连叔,我怎样才能心安理得的“躺平”呢?
一条心甘情愿的咸鱼
一条心甘情愿的咸鱼:
在国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当领导,就是通常所说的“当官”,绝大多数人及其家庭是不会拒绝的,是渴求的。你家给你的压力并不特殊。
可是,这绝大多数渴望当官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想清楚当官的本质是什么。一旦想清楚,他们可能害怕当官。
当上了官,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好官,二是坏官。
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结党营私、吃拿卡要、骄奢淫逸、作威作福、尸位素餐、昏庸无能,这都是坏官。老百姓极度厌恶。不过,太多想当官的人,潜意识、显意识,都是冲着这些去的。当百姓时,讨厌当官的,当官时,却非要让百姓讨厌。不可否认,官场一度是的,不少人明目张胆当坏官。更不可否认,权力会永远诱惑人当坏官。可是,这条路走不通了。无论你是原本就想坏官,还是逐渐被诱惑成坏官,现在风险都很大,担惊受怕是常态,东窗事发后,身败名裂,牢狱之灾,累及家人。这怎么是人做的事呢?这是鬼做的事。或许有人认为,自己可以非常巧妙地,同时又逃脱惩罚。即使侥幸做到,你不觉得很猥琐吗?这么大的聪明,干什么不成就一番事业,用来占这点便宜?
当官就要当好官。一个好官,就是小到乡长,小到只管几个人,你也影响他人的命运,让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再小的好官,都功德无量。可是好官也不好当,一是要有那本事,二是必须无我无私,让你加班就得加班,私企员工可以抱怨996,你007都是应该的,你要牺牲自己,牺牲家庭,你是人民的,是国家的。这种日子不是过一天两天,而是过一辈子,即使在最后一天你忍不住成为坏官,也要受惩罚。这怎么是人做的事呢?这是神做的事。你要放弃许多普通人的乐趣与权利,要更高尚,更纯粹,没有低级趣味。
你意识到自己当不了官,只想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怎么是躺平,这是通透的智慧。普通人过好日子,也是需要智慧、纪律和耐心的,才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中不忘初心,不瞎折腾。任你如何诱惑,我只孝顺父母,培养孩子,夫妻恩爱,这是超强的定力,是普通人获得一生幸福的大本事。
祝开心。
连岳20230228
《人世间》一切自有安排,命中注定周秉昆不能做官
要问《人世间》谁的命最好?都不用查星座,掐指一算非周秉昆莫属!
说他命好,不是说他这一辈子有多么飞黄腾达;恰恰相反,要庆幸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平安度过平凡而普通的一生。
周秉昆这人,很讲哥们义气!
讲义气的人,总是朋友很多;朋友很多,麻烦事当然也就多!
周秉昆为龚兵工种的事找曲秀贞,当然给曲老太太给顶回来了;
周秉昆为孙赶超家搭建房子的事找龚维则;
周秉昆为龚维则停职的事找曲秀贞;
周秉昆为蔡晓光上学的事找郝冬梅,使郝家对周家产生长久的猜忌;
周秉昆为国庆爱人于红招聘的事找蔡晓光;
周秉昆为国庆姐姐工作的事找邵敬文;
周秉昆为孙赶超妹妹工儿的事找白孝川
……
周秉昆虽然生活在底层,但他有当官的哥哥;做教授的姐姐;还有人生中的贵人如曲秀贞、白孝川,这些都是很有能量的人。
作为朋友,那是没得说,周秉昆绝对是个好人。自己能量虽然不大,周围有能量的人却不少,而且周秉昆踮踮脚,还能够着几个。
他这种性格,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手中有了权力会怎么样?不用墨子多说大家都猜得到,最后一定是公器私用,公权力就成为他解决亲戚朋友困难的专利产品了。很多出问题的官员,都曾经是“很热心”的人,都很慷慨为朋友“排忧解难”的人。所有的网不都是这样织出来的吗?
大家是否记得,周秉昆从监狱中出来,朋友们为他“洗尘”, 周秉昆突然站起来,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要对大家道歉。我原以为我哥哥会和关照我一样关照大家,结果他没有!
这话叫人听的,既感动;又震惊。
像周秉昆这样的性格,一旦有个官身,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官呢?就像周秉昆的朋友评价他的哥哥周秉义:一心只想着做官!或者像郝冬梅的父母那个,冷眼看世界,斩断一切可能的麻烦。虽然令人不悦,但不失为官之道。
当然如何做个好官,命题太大!不是小民要操心的事!
周秉昆运气很好,他不是官,所以杜绝了他犯错误的机会;
周秉昆命也很好,他是老百姓,但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有不是普通人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
过年时这些人拿过来的年货沿墙脚堆了一地,在那个年代普通人都没见过;而周秉昆还可以拿来分给一帮朋友们。
他自己人在监狱的时候,儿子周聪的工作有人帮忙解决。
拆迁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大的实惠。房子店面一下子都有了。
想来想去,周秉昆是个普通人,但也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
他这个人,不能做官,所以安排他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这个人,喜欢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他后面站着不少超级能量的人。
这样的好命,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如《增广贤文》里所说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