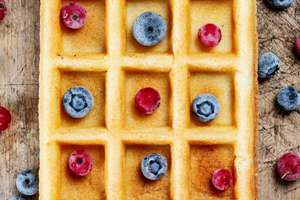赵忠祥八字(赵忠祥八字命理)

细思极恐!私生往男星车上装后,被扒动作熟练完全不怕被抓
饿了吗?戳右边关注我们,每天给您送上最新出炉的娱乐硬核大餐!每个明星似乎都会有几个疯狂的粉丝。
8月5号,曾参加过《青春有你》的男偶像徐炳超突然发文,称“在车上安装不是法律允许的行为,希望能尊重我,这样做也会给我的工作和合作方带来困扰”,最后一句“这样好玩吗”连接四个问号,明显带着怒气。
他放出图片,车盖上一个黑色的长方体,应该就是从车上找到的。
徐炳超说想让人尊重一下他,其实这句话的对象是私生粉,即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跟踪偷拍明星的那一类粉丝。
粉丝心疼他,在下面评论“希望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同时还有人表示,这位放的私生已经被拍到了照片,希望她能好自为之。
网上曝出一张模糊的动图,那个私生粉在司机的眼皮子底下往车上装定位器,她的动作熟练很淡定,看着令人感到可怕。
不过曝图的人还是很善良地为私生打了马赛克,保护她的隐私权,网友们看到后都说“这种人不配打码”,建议公司报警抓人。
其实徐炳超的名气并没有太大,在当偶像之前他是个小模特。
2017年他参加模特大赛获得总冠军出道,之后去米兰、巴黎等地的时装周走秀,直到2019年参加《青春有你》,止步于20强,没能成功出道。
后来他与谷蓝帝、胡文煊、师铭泽、丁飞俊这四人一起组了个组合“沙漠五子D5”,属于饭圈里有名字,但路人看来根本不认识的男团。
就这样一个糊到看见名字都要问问他是谁的小爱豆,竟然也有人往他车上装,网友感叹现在的私生真是疯子,直接往车上放太大胆,根本不怕被抓。
所以细想一下,爆红的明星只会遇见更可怕的私生。
的确,娱乐圈里被私生粉骚扰苦不堪言的人实在太多。
同是选秀出身的黄明昊,曾在网上说“距离产生美,酒店蹲点就算了,不要上到我房间门口呗”,劝私生别堵门口。
曝出的照片里私生趴在酒店门上,看着真的很吓人,这让房里的人如何安心休息。
还有肖战被私生摸手、王一博被私生不停打电话骚扰以及朱正廷遭私生按门铃,许多流量明星都被私生折磨。
倪萍老师最近在节目《倪吧拉呱》里说到了粉丝追星观,她曾和赵忠祥老师在签售时遇见疯狂的粉丝,人多到将书店的玻璃门窗都挤碎了,然后倪萍老师送上八字箴言“理性追星,量力而行”。
这次徐炳超被私生在车上放,私生的行为应该能算违法了,也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维权报警呢?
#私生在徐炳超车上装#、#青春有你#、#徐炳超#
作者:李西西
责编:饶舌歌手阿瘪
娱乐圈新动态【徐怀钰】42岁徐怀钰现身商演!楼盘门口简陋随意,笑容满面又唱又跳显娇俏
【陆毅女儿】陆毅俩女儿长大啦!贝儿长腿吸睛快有妈妈高,妹妹憨厚可爱气质好
【杨澜】52岁杨澜翻车了?大谈与老公和谐相处秘诀,却连结婚时间都说错
平凡的世界三
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想,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 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他只从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 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中拿出五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 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 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 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他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就要复查! 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揩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气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 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得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时间约摸快到七点半了。
他找到了八号楼。他从四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他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吃饭,上楼时两条腿很绵软。 黑暗中,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揩了揩苹果上的灰土。 现在,他立在三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 他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 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 他终于轻轻叩响了门板。 好一阵工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面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女大夫! “你找谁?”她板着脸问。 她当然不会认出他是谁。 “我……就找你。”少平拘谨地回答,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什么事?”“我……”他一时不知该怎说。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 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我有点事,想和你说一下!”他哀求说。 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他放进屋来。 他跟着她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什么事?”女大夫直截了当问。从她脸上的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 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血压怎?”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他坐下。 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 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 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 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一百六十五。就是你为我量的……” “噢……”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静地说。 “如果还不合格呢?”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 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 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他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 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对不起……”他用手掌揩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揩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女大夫突然问。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工。” “上过学没有?”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当过教师?” “嗯。” “那你……”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万一再紧张呢?”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他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他手里递,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孙少平一怔。 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 他绊绊磕磕下了楼道,重新回到马路上。 他解开上衣的钮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
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 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到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七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 他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 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土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 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坬坬、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 不仅大牙湾,铜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 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 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
这院落连同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搁着许多日用杂物。 “你找谁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他。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拉住他的小胖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明明,王明明!”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才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 这时,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大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你找谁?”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 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一两毛钱的醋?”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河南大哥咧着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街上的门市部关了……”少平解释说。 但他实际上还没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 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 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 “走,进屋去坐!”王师傅过来拉住他的胳膊。 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他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 “兄弟,先喝一杯!”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 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 一时三刻,这夫妻俩就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 过了好一会,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 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他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 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地刺疼。 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 他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惟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桅林似的自制电视天线…… 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 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 前面的三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
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他的光胳膊上。 他像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 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 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弛下来。 女大夫盯着血压计。 他盯着女大夫的脸。 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他听见她说:“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十……”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 “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 他向她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他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噢,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