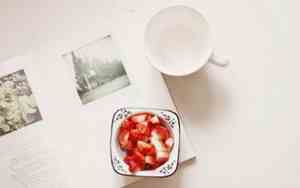浈(浈江区)
刘光华丨浈江河(散文)
浈江河
□刘光华
说南雄,不能不说到南雄人的母亲河——浈江河。
南雄地处山区,浈江河是一条流经县城城墙脚下的河流。一百年多来,我家有三代人依江而居,与浈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自爷爷入粤起家族中的第三代。打从一出生,我就在河岸边看惯了浈江水涨水落和江面上的船来船往。我的童年写满了这条江河的记忆。浈江不仅记录了我家的百年往事,同样,镌刻下我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住水南。看城墙,看宝塔,看城墙下游移的篷船,看沿河的绿榕翠竹和日出时的“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河面风光。
长大后,入了城,住到了城墙上。我又看到了水南的村落和起伏的群山与成片的稻田。
童年的记忆是永恒的。一说起童年,没有哪一个地方有故乡的河记忆如此深刻,没有哪一个地方能让我对儿时的故乡魂牵梦萦。每当说起故乡,我的脑中就会流过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的祖国》
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心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
年少不知词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唱着歌,读着诗,我似乎回到了梦里和童年的故乡。歌与诗恰如其分地描绘和表达了我小时候故乡的情景和情愫。
最难忘,浈江河下的那片长长的细沙滩。沙滩是我童年的桃花源,那里有我的欢乐、梦想和脚印,以致今天想来,童年的沙滩确实让我回味一生。童年时有过一片属于自己的沙滩,真乃我的人生幸事。出家门,迎面是一围厚实古朴的城墙,轻移几步,又见一条清澈的大河,走过空坪、跨下石级,越过竹丛,接着就到了绵长的沙滩。多么可爱的沙滩啊,又长又大,沙滩从从家门一直伸延到南雄大桥下,从水南的土岸漫到了江心。
浈江河几乎是半江沙滩半江水。河水从上游的三洲、五渡来,过南雄大桥后,突然一个急转弯直向顺水码头,接着紧贴着城墙根,流过盐码头、龙蹲阁码头,当河水在龙蹲阁码头回旋片刻后,又突然一个急转弯,直冲着对面的水南村榕树下的河堤而去,流过天阎公粮仓后,又折向青云码头。浈江河在城墙下左一弯右一折地折腾后,接着又从青云码头冲向对岸。这时河水又贴着南岸缓缓流向铁丝桥和河南桥。从青云码头和槐花码头城墙以下,又多了一片长长的碎石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城里的居民在干旱季节走下城墙来种菜。一年之中,逢上雨水季节,浈江河洪水暴涨,河水淹没沙滩,甚至漫上河堤,但大水过后,浈江河又恢复常态,裸露出一片整齐细柔的沙滩,年年如是。因此,故乡的河和门前的那片沙滩就这样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天气炎热的夜晚,河风送凉,星河灿烂,水南村的孩子似乎都跑到了沙滩上。他们唱着古老的儿歌:“月光光,照四方,四方暗,跌哈坎,坎头一枚针,检过婆婆做观音,观音面前一口塘,一只鲤哩八尺长。”“羊咩咩,羊格格,老婆(BO)开门大脚射。”孩子们尽情地在沙滩上追逐、嬉戏,欢乐的童声回荡在河岸的上空。这时,在沙滩浅水处,有人提着油灯,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用叉子叉游到浅水来乘凉的小鱼。多么美好的夜晚。孩子们玩累了,一个个先后回去了。但我依然舍不得这满天的星斗和迷人的沙滩。有时用冰凉的细沙流过光光的小脚,有时仰面躺在柔软的沙滩上,一遍又一遍地默数璀灿的星星,数着数着,脑子就野马般地跑远了。
那时候,正值“”,学校关门,老师挨斗,学生不用上学。孩子们很无聊,沙滩和星空就成了我打发时间和发呆的地方。
住在水南,朝晚对着沙滩、城墙和城央的宝塔,怎不引起少不更事的我的无数遐想:为什么会有城墙?城墙什么时候建造?人要是爬到宝塔顶上面多好啊!有时,我又会对着脚下的河水发呆:河水从哪里流来,河水又流到哪里去?爱幻想的我就这样一遍遍地想。心里有怪怪的想法,但却不知用言语表达,古朴的南雄和悠长的河水就把一颗童心带走了。
那时的县城很安详,河水很宁静。有一年,因为河里涨水,水运公社的一位社员在城墙上向着水南喊话,开始人们不明白怎回事,后来才听清他是向水南村的船民发通知。
那时的县城很美,日出日落,把古老的山城照得金碧辉煌,把一江碧水照得金光闪闪。
那时的天空很洁净,一抬头就看见蓝天白云,一入夜,就看见满天星斗。
那时的世界很小。每天看见的河水,波澜不惊;每天走在的乡道上,所见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每天对着的老榕树、老城墙、老码头、老宝塔和淳朴的乡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熨贴和舒畅。城乡人已习惯了鸡犬相闻的日子。日子过得象浈江河上移动的篷船,不紧不慢,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浈江河的篷船也象一幅变化的风景画,时而停泊于城墙下,时而移近到浅水边。有时,在江面上,还会看见一只载着鸬鹚的竹伐在城墙下捕鱼。城里人每天都会走出城门孔,走到码头来洗衣、洗菜和挑水,夏天到了,孩子们在一个个码头上跳水、游泳,开心极了。风清水浅的日子,大人们卷起裤卷涉水入城。村里的年青人吃过晚饭,也常常涉水进城逛街看电影。那时候,看电影是城乡人唯一的也是最吸引人的娱乐。电影散场后,人们又说说笑笑地涉水回家。那时的老南雄乐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不知道山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一个个都爱守着宝塔过桃花源的生活。
童年的时光很短暂。依河而生、依河而长,当我长到似懂非懂事的时候,父亲给我特制了一对小木桶,学着大人的样子,走下河岸去河里挑水。扁担一上肩,我的肩膀就越来越沉重,渐渐担负全家的食用水,而且从水南村挑到住进县城。十多岁起,又常常到父亲的工厂挑柴。父亲每次在厂里买了柴,我就象蚂蚁一样,在水南和家之间往返搬运,每挑一担柴就要绕一个大弯从南雄大桥走过。此外,我还到工厂给爷爷挑河水冲凉,给家里的菜地淋菜。
挑水挑柴几乎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家务。直到我上高中住校了,那根跟随我多年的扁担才从肩膀缷下。孩提时代,我七、八岁开始就给在厂里加班的父亲送午饭,若是逢上父亲在河边给船家修船,我还得顶着烈日踩着滚烫的沙滩送饭到河边。我不记得小时候我有没有穿过鞋,因为从小我就穿木屐,所以,我每次走下沙滩,我的小脚丫就被烫得蹦蹦直跳,好不容易才走到河边,恨不得猛地跳进清凉的河里。
苦难的浈江河,见证了当年的一对小脚丫和一副稚嫩的肩膀在沙滩、河堤和城里的河边街奔跑。或许是少年劳苦功高,多年以后,父亲于闲谈时特给我两个荣誉封号:“运水仙官”和“担柴童子”。
浈江河,我的母亲河,一条欢乐与苦难的交织的河!为了帮补家庭,父亲有时会带着我到上游的水口桥的村内买竹子,在竹丛砍下竹子后,扎成一个小竹伐,顺着浈江河拖回家。父亲常常利用工余时间在油灯下刨“马筋”。(“马筋”是一种用来塞船板之间的缝隙材料)。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父亲有时带着我到浈江河网鱼。夏夜,还跟着父亲和他的工友到浈江河照鱼。他们点着几蒌油性很强的松木,沿着河边,借助火光寻找停泊在河边的鱼儿,一旦发现了鱼儿,就用叉子猛扎。有些鱼儿比较警觉,发现火光来了,就急速逃离河岸,大人们提着火蒌,手持钢叉,穷追其后。刹那间,一场追逐与逃亡的较量就在漆黑的沙滩边展开。夜深过半,照鱼人才从三洲、五渡徒步归来。
浈江河啊,呜咽流淌,日夜唱着一首忧伤的歌。
母亲河也有一反常态的时候。几场大雨过后,浈江河水暴涨,洪峰来时,浑浊的河水从上游铺天盖地而来,大水浸到了半城之高,淹没了城门孔,有过一、两回,洪水还漫上了河边街来。这时洪水摧枯拉朽般地猛撞南岸,水南村岌岌可危,洪水浸没了老榕的主干。但村里没有房舍被淹。那时候,家门口成了一片汪洋世界,好不惊心动魄!浈江河每年都会发上几场大洪水,两岸的居民似乎习以为常。城里人听说涨水了,都纷纷爬到城墙上看热闹。我也喜欢站在家门口对着洪水发呆,看一个个泛着白色泡沫的水泡不断地在眼前漂过。这时,突然有十几挂木排和竹排在从上游呼啸而来,顿使我如梦方觉。那一方方连体木排如一个个方阵,如从天而降,排头的放排人手持竹杆,目视前方,挺拔而立。当我还处在惊魂未定时,甚至连他们的脸庞还没看清,这猝不及防的一幕就在我眼前一飞而过。那情景,简直是电影里的惊险场面,英武的放排人让人羡煞死了,但又使人的心快提到了嗓子眼了,真是令人回肠荡气。
端午节前,浈江河总要下上几场大雨,面对屋外淅淅沥沥的雨水,大人们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龙舟水要来了。”老南雄已习惯了季节的变化,洪水一来,有人就带着渔具出门,蹲在岸边溪口“搬鱼”。接着是龙舟下水,为当年的龙舟赛作准备。那时,水南村有两只龙舟。一只龙舟神气活现的龙头,栩栩如生,另一只是外号为“勾鼻子”的龙头。那时农村还很穷困,据说那个神气活现的龙头还是从广州花“巨资”买回的,“勾鼻子”是当地木工制作的龙头。
每年,水南村都要举行隆重的龙舟下水仪式,祈福当年风调雨顺,消灾消难,五谷丰登;同时也祝愿当年龙舟赛获胜。当村民们把龙舟从昏暗的老房子抬出推下老榕树头下的河边时,那场面可动人啊,大家齐心合力,如猛虎出山,声震山城,瞬间打破往日的沉寂。这时的水南村又敲锣,又打鼓,鞭炮齐鸣,孩子们过节似地兴高采烈、奔上奔下:“要划龙舟了,要划龙舟了!”我不知道浈江河上的龙舟赛始于何时,但我却知道这古老的民俗一直为老南雄沿袭到改革开放初期。水南村和水西村互为对手,早已憋足了劲头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决心要在浈江河上一试身手。龙舟比赛那几天,全城轰动,万人空巷。浈江河上,鼓声喧天,人声鼎沸,沿河上下、城墙岸边,挤满了看龙舟的民众。当龙舟从下游越来越近水南时,鼓声越来越响,人流也渐渐向上游移动。人群中有人说:“来了,愈来愈近了。”有的说:“看见了,看见了……”看龙舟,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好的位置都被大人们结结实实的人墙挡住了,我们只好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赛龙舟是老南雄的一大民俗盛事,赛事过后,街头巷尾还能听到老南雄说上好些日子。
初期,父亲在城里买了一间老房子,从此我家住到了城墙边上。我与母亲河真是有缘,虽然搬家了,但依然临水而居。更有意思是,小时候从水南隔河看城墙和宝塔,而今家就在城墙上,置身阳台,侧身能见高高的宝塔,俯首能见城下日夜厮守的浈江河。
进城的第二年春天,我家的客厅就来了燕子。这下可把孩子们乐坏了。我当时不明白,燕子怎么会飞到城里来?当我去大街的外婆家时,发现外婆隔壁人家的楼梁上也有燕子筑巢。燕子双双来时,在大门下飞出飞入,衔泥筑窝,没过多久,燕子窝有了小燕子。当我们从厅下走过,常常能听到头上嗷嗷待哺的雏燕的叽叽声,在燕子窝下的地面,常常有一滩从窝上掉下的白色的粪便。
进城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我家的那一方露天阳台,我爱站在阳台边,看对面连绵群山,看脚下蜿蜒河水,看水南村落的炊烟,听对岸树林传来的鸟声。渐渐地,我明白了,老南雄实际是与乡村一河之隔。春天一来,燕子只要稍稍抖动一下翅膀,就能飞过江河,飞入寻常百姓人家。
父亲当年在城里买房一定是出于多种考虑,但有一点却是父亲可能没想到的,那就是房子的旧主人临走时候留下的一堆又旧又破的老书成全了求知欲极强的正值少年的儿子。
进城后,我把儿时的沙滩抛到了脑后,从此一头扎进了老屋的旧书。多少日子,我从河里一挑完水回来,就三步并两步跑上阳台静静地读书。夕阳西下,我读书读得连河对岸粮仓树梢上的鸟鸣声也充耳不闻,那时刻,我完全沉浸于书的世界。忘了时间,忘了身在何方,直读到河南岭天边悄悄隐退的最后一抹晚霞。
感谢上苍,给予我儿时一个嬉戏的沙滩;感谢上苍,给予我少年时一方读书的阳台。
春雷一声动地响,时逢春雨,万象更生。我终于有一天要走向山外,临别的那个晚上,我默默地对着浈江河说:“别了,生我养我的母亲河,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看你!”
2020-6-24初稿2021-7-24一校2021-8-5二校2021-8-21定稿
作者简介:刘光华,1957年生,广东南雄人,现居广东中山。中专教育学高级讲师,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一生教书、读书和写书,一生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为书路人生。著述《刘光华文集》,分教育教学、家庭教育、学生心理咨询、文学、游记等13卷,于2017年5月20日公开出版。
编辑出版:@今日头条@中山文苑
责任编辑:张勇轩
运营人员:齐速
☆☆☆☆☆☆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