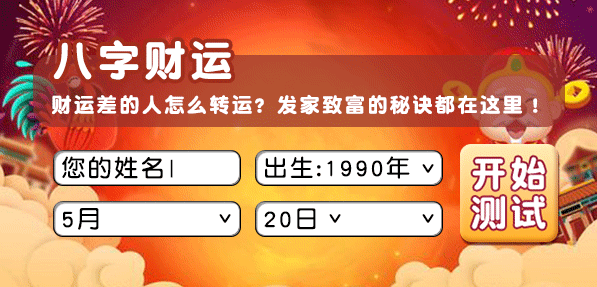八字三两七钱(八字三两七钱女命)

古时候流落青楼的女子如落叶成泥
已完结
平淡的小故事
我五岁就入了花楼,因着我阿娘去了,小弟还嗷嗷待哺,我那阿爹还等着娶新妇。
便将我以三两七钱的价格卖入了烟花巷的轻屏楼。
当时我拽着阿爹的裤腿可我爹一脚就将我踹开,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那个家,只是我差点咬下他一块肉。
老鸨吟娘皮笑肉不笑的说了句「是个狠心的女娃,连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敢下狠口。」
吟娘指着龟公就要把我扔进柴房想让我关几天磨磨我的锐气。
我就直接跪下向着吟娘磕了三个响头「您放心,您买了我,您就是我的主子,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两岁就会喂鸡,劈柴,就连我弟那身上的尿布都是我洗的,我保证让您这银子花的值得。」
听完我的话吟娘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是让我伸手给她看看。
便领着我去了一个花娘的房间,吩咐着花娘对我用心些。
这是我第一个服侍的花娘叫梁䒩,「你今年多大了?」这是梁䒩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五岁了三个月前的生辰」我揉着沾土的衣盯着打着补丁的还略大鞋不敢抬头。
「看样子是个勤快的孩子,我留下了,谢谢吟娘。」
吟娘摆了摆手「这孩子有点牙尖嘴利,你自己小心些。」说完就出了梁䒩的房。
梁䒩放下对外人的假笑,戳着我的脸颊说到「比我进花楼的年纪小上不小呢,我十二岁进了花楼十五岁就开了苞,至今在这都有七年了,你以后也就是这样的命了,懂吗?」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看着梁䒩穿着锦衣戴着金钗,我点了点头从此就在花楼住下了。
我看着每天在梁䒩房里进进出出的男人,看过梁䒩不着寸缕的衣服下青青紫紫的模样。
一直到我八岁时,梁䒩没了,是个特别平常的日子,有个屠户“喜欢”梁䒩却又不想使银子将梁䒩包下来。
和我一样每天蹲着看着梁䒩房里进进出出的男人,那天便趁着梁䒩才接完客我去打热水时闯进了她的房里。
拿着被子捂住了梁䒩的嘴解着自己的裤腰带就想硬上,一不小心力气使大了,梁䒩没了挣扎。
我回房时梁䒩身子已经有些僵了,那屠户还在梁䒩身上起起伏伏。
我大叫着吟娘, 吟娘急匆匆的赶来脸上的胭脂还没晕开,看起来像我弟弟红着的屁股,可笑急了。
屠户听到我的喊叫,裤子都没穿上露着屁股跑下了楼。
但吟娘高呼着打手关住了花楼的门,将屠户打了一顿扭送进了官府。
那是我第一次见官老爷,官老爷年岁不大是前年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第一次审人命官司。
但听到死的是个花娘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下跪何人,所求何事。」
惊堂木拍着桌上的声音,我忍不住抖了一下。
吟娘按着我的手说到「青天大老爷,奴家是青屏楼的花娘叫吟娘,那白布盖着的是我们的花妓梁䒩,今日接客后被这人偷摸闯进了房,硬上了后捂死在了房中,这是他在我们花楼写下的证词,还请大老爷过目。」
吟娘不卑不亢的举着证词,师爷将证词递给官老爷过目。
官老爷命人,掀开了白布,看到梁䒩的脸忍不住惊到了。
她的脸惨白着,眼睛睁着像是含着不甘,梁䒩的衣服是吟娘和我费力穿上的,死人真的比较重,这是当时我心理的想法,但是我看着梁䒩的脸什么都不敢说。
因人证物证都有,屠户就被判了秋后处决,官老爷搜了屠户的家赔了十八两银子给吟娘,吟娘又组织花楼的姐妹湊了二十三两给梁䒩找了块地简单埋了。
因梁䒩死了,花楼的娘子觉得我不吉利,个个都不想让我伺候,我便做了一年的扫洒女,烧火、劈叉、浆洗其他丫头不愿意做的活都会扔给我。
直到我们花楼新进了一个花娘,她是吟娘从江南买回来的瘦马,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古琴。
因为人太过高傲,脾气也大,花楼的小丫头跟着她三天两头的不是被打就是被骂,就没人愿意跟着她,纷纷跑到吟娘那诉苦。
吟娘便将我领到瘦马面前,「这是我们花楼最后一个没伺候过你的丫头了,你在把她打走,就自己去人牙子那买吧。」说罢便把我扔她房里了,扭着缸宽的腰下楼去了。
我跪在瘦马的面前,「我知道你,你是之前花楼哪个死人的丫头,他们都嫌你晦气,我不讲哪些,只要你伺候好我就行。」
我低着头,嗯了一声。
「头抬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我头抬起来看到了瘦马的脸,她真的长的很美呀,那樱桃小口,弯弯细眉,酒窝里酿着的笑可以让男人醉下。
「我没有名字,我阿娘唤我野娃,花楼的人都喜欢叫我娃娃。」
「的确不是个名字,以后你伺候我,就叫叶子罢了,以后我就是你的主子,我叫萱花。」萱花给我改了个名字,她是鲜花我是她的丫头也就是叶子。
过了一个月,吟娘要给萱花了,萱花是她花了五十两银子从江南买回来的,这一个月给萱花造势又花了不少银子,所以萱花的价比其他花娘的价格都高,要二百两银子起卖。
萱花知道后掐着我的胳膊,知道我痛呼出声变踹了我一脚,没站住脚就倒在地上,但是我不敢出声了,这一个月我知道了萱花的厉害,她喜欢听别人痛苦的呻吟,见我没声音就,她又踹了两脚才叫我滚开。
「叶子,你听过我弹琴吗?」萱花摸着她从江南带过来的古琴,脸上有着平时不见的柔和。
「听,听过,小姐在房子抚琴时,奴婢在门口听过,很好听。」我说不出什么形容词,只知道萱花弹的琴是花楼中最好的。
「我学了十二年的琴,学了十二年的服侍男人的本身,今天就要用上了,二百两银子啊,我当时被卖做妓时连个零头都不到,我才四岁就被我哥卖了,要换银子给他娶媳妇,今年左不过十六岁就要变成千人骑的妓子了,叶子,你以后也是,也会变成我这样的。」说罢,萱花就拿起了剪子将琴弦一根一根的剪断了。
我不敢看萱花,因为我知道萱花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清泪,搓着我的衣角,转身去给萱花那毛巾擦脸。
吟娘带着花楼的妆娘敲开了萱花呢门,看着萱花不咸不淡的表情说到,「今天算是你的大日子,你可别摆着这苦样子去见客,初夜卖不出好价钱,你往后的日子可会辛苦多了。」
初夜拍的价格越高,往后客人上花楼卖的价格也会越高,我们花楼最以前价格最高的是梁䒩一次的价格是六两,最低的也要一两七钱银子一次。
可是花娘们被吟娘压着,拿到手的皮肉钱却少的可怜。
梁䒩每月能领到二两银子,我每个月只能领到五文钱,梁䒩去了后我变没了月钱,直到跟着宣花后吟娘还给我涨了五文钱,我每月便可以领到十文。
没多久宣花就被妆娘装扮好了,我守在宣花的门口,看着在台上弹琴的萱花,思绪不知飘往何处,台下的男人摩拳擦掌,一曲毕后萱花上了楼,我给萱花开了门,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不甘的泪,我也不敢出声安慰。转身关住了萱花的门。
「今天啊是我的萱花初夜拍卖,价高者得,起拍价二百两银子,各位大爷可要好好拍哦。」吟娘的嘴都要咧到耳后了,手帕子一扬,台下的男人们开始竞价。
「二百二十两」
「二百三十两」
「二百六十两」
……
最后的价格定到了七百七十两银子,那个男人我知道,是花楼的老客了,城中最贵酒楼老板的独子许承詞,是个被酒色掏空的花花公子。
吟娘领着许承詞上了楼,我守在门口,听到萱花和许承詞的调笑,萱花的的一声轻呼,我变捂住耳朵,蹲在墙角数着数字,不敢再听房里的声音。
那夜,我蹲的腿都麻了,困倦了,醒来时天已经有点亮了,想着萱花起来要用热水,我就赶忙去取了热水,在回来时萱花已经起了,许承詞也早走了。
我伺候着萱花沐浴,萱花白白的皮肤上是一些红红青青的印子,「你去把床单换了吧,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是,小姐。」我停下了淋水的手,串过屏风,看到帕子上的红点,将帕子收起来等下要给吟娘的,这是女子的第一次,吟娘都要过目给花楼中的丫头们看,让丫头们知道女子的第一次可以买出好价格,不至于被其他男人骗了,欺了身子破开了就卖不出价格了。
萱花拍了初夜后,也吟娘也没让她挂牌接客,我才知道萱花哄着许承詞找吟娘包下了她一个月,许承詞可是花了不少银子,萱花在这一个月也是使劲浑身解数,将瘦马的技巧哄着许承詞留恋忘返。
可没到一个月许承詞就从家里偷了妻子的手镯卖了个一千四百两银子,又添了一些银子找吟娘赎了身。
萱花就离开了花楼,她本想要吟娘将我也赎出去,因为我是跟着她最久的丫头,但是许承詞拿不出多的银子,觉得我还小也没什么姿色,便不让萱花多嘴。
就这样我还是在花楼,吟娘没让我去扫洒了,让我跟着珂珂伺候她了,珂珂是个良家女子,是吟娘从人牙子手中买回来的。
虽然珂珂没有萱花长的那么惊艳,可是混身散发着清冷的气质,会写字、弹琵琶、还会女红。
「珂珂,以后叶子就是伺候你的丫头了,你也别不认命运气好的话,你还能像萱花一样,初夜拍卖后就直接被人赎走了。」吟娘劝着珂珂。
珂珂流着清泪,清冷的美人落泪,着实招人疼,我都忍不住想给她擦擦眼泪。
「你也别哭了,这花楼里的姑娘也没有不哭的,哭过后就认命吧,过些日子就是你的初夜了,好好休息,拍个好价格,今后自己存钱也能把自己赎出去哈。」吟娘拍了拍珂珂的肩膀,让我上前伺候,边转身出房下楼去了。
「小姐,我是叶子,我什么都会也不怕疼,您要是心理不得劲,许打我一顿也就好了。」我伸出胳膊一副认命的模样。
珂珂抬起头看着我,「我不打你,你不要害怕,我如今也是浮萍,我今后只能是一个花楼的妓子了。」
「以前你伺候的哪些人经常打你吗?你不害怕吗」珂珂止住了眼睛,红着眼睛盯着我看。
「不,不是的,奴婢只是看着您心情不好,想让您打我出出气,这样您的心情会好很多。」我揉着衣角,低着头不敢再看小姐的眼睛。
「你我都是苦命的人,我不会打你出气的,放心吧。」珂珂叹了口气,扯着嘴角想向我扯出笑容,可惜挤不出来。
「谢谢小姐,我去给您打热水梳洗一下,您先吃饭吧。」说罢我便下楼打热水去了。
伺候珂珂的日子是我在花楼做丫头做快乐的一段时光,珂珂会教我认字、读诗、给我打扮,我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可是漂亮在花楼不是好事情,我发育了起来,珂珂十五了却还没来葵水,一直在花楼做艺妓,直到珂珂的竹马赶到了花楼,我才知道珂珂原来是青州何员外家的嫡女,何员外是皇商,可惜得罪了宫里的娘娘,男人被充军,女子则被发卖贱籍,珂珂因气质样貌良好被吟娘买了回来,其他的庶妹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日我记得天气很晴朗,花楼的姑娘还没睡醒,珂珂的竹马就踹开了花楼的门。
吟娘差点唤打手要将竹马打一顿。
珂珂在楼上轻呼「渝郎。」
那渝郎才放下手中的凳子,珂珂眼中含泪,急匆匆的下了楼。
吟娘命我将珂珂带回房中,我拉不住珂珂,也不想阻止她和情郎相拥,吟娘拉住珂珂不让她向前。
扭送着珂珂上了楼,渝郎看到珂珂被吟娘抓着也不敢乱动,静静的看这吟娘将她拽上楼关了门,让我守着门口,不许珂珂在出去。
我等着吟娘下了楼,看着吟娘将渝郎带进自己的房间,珂珂在房中抽泣,我不忍但也没法放珂珂出门。
不过半晌,吟娘变满目春风的将渝郎迎上楼,命我开门。
「渝郎。」门开后珂珂和她的情郎相拥在一起,渝郎恨不得将珂珂揉进骨子里。
「哎呀,珂珂你呀真是命好呀,穆公子拿着银子来赎你了。」吟娘笑的见牙不见眼,我才知道渝郎尽然为了珂珂去当了兵,这一年多不停的打听珂珂的消息,又在战场上不停的英勇杀敌,混了个小官职。
回城后又是求父母,求祖母要银钱将珂珂赎出,老一辈的也一个他们是真心,就同穆毅渝说了三个要求,若珂珂清白不在不可赎,珂珂赎回后也只能做外室连妾也是不能做的,最后一条不能留子嗣。
穆毅渝知道这样对珂珂不公平,但也只能点头答应,毕竟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将人赎出。
吟娘和穆公子谈好了珂珂的价格九百五十两银子,今日便要将珂珂带走,我看着珂珂眼中满是不舍。
珂珂是花楼中待我最好的小姐,从未苛责与我,还教会了我识字,打扮干净自己。
珂珂也想将我赎出,可是吟娘要的价格太高,要五十两银子,珂珂难住了,五十两银子可以买好多丫鬟了,她没钱,也没办法开口找渝郎要钱。
「小姐,你不必为难,叶子知道自己的命,如今您已经可以脱离这里了,叶子只会祝愿您今后的日子幸福美满。」我拉着珂珂的手,露出认为最好看的笑容,趴着珂珂的腿上。
珂珂没说什么了,只是叹口气摸了摸我的脑袋,变不在说话了。
珂珂将她的衣服首饰都留在了花楼里,将最好看的簪子给了我,祝愿我今后也能遇到良人。
珂珂走后没多久,吟娘也没让我做丫头了,反而是给了个丫头我使唤,我知道自己快挂牌了,便收了心不在多言。
此后花楼不停的在进新人,也有不少花娘被赎出,吟娘终究是年岁大了,对花娘宽容了不少,就连年岁大了的花娘也想办法给她们找出路。
过了两年,我十五了来了葵水,相貌出落没有萱花好看,也没有珂珂冷清的气质,但是我有一双上挑的媚眼,窈窕的身段,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落燕。
慢慢的我学着萱花的姿态一个媚眼便将男人迷上后,吟娘要我拍卖初夜了。
在我被拍买初夜那日,我看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也有一些文邹邹的书生被推来看拍卖,吟娘看着台下的客人喊着价格「八十五两银子。」是我初夜的价格,真贱啊。
台下不少人竞价,我最后的初夜竟被拍卖出了四百二十两的价格,拍下我的是个书生。
白白净净看着就是个小雏鸡,当时我心中想着,随后他便摸上了床,解开我衣领脱下亵裤的手极为熟练,就这样我也成了个妓。
不知是不是珂珂保佑着我,不过在花楼挂牌了半年,有个商户就过来赎我了。
他是个行货的商人,在水上行商,常做书生打扮,因为他爹一直想让他高中状元,可惜他不是块读书的料。
后我被他以五百两银子赎出,跟随着他一起行商后才知道,他要的不是个小妾,而是一个会伺候人的妓。
我跟着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要是酒桌上有人看中了我,他便会将我送到那人的床上。
一次又一次,直到我怀孕了,孩子不知是谁的种,他也不会让我留下,生了孩子身材就会走样,我就没了价值。
一碗堕胎药灌进我的嘴里,我挣扎不了,喝了后我狠狠的咬了他一口。
他把我摔下床榻,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我的身体像是不停的往下坠。
抬起手鲜红鲜红的血,慌着我的眼,我像是看到我的阿娘。
她是被阿爹活活气死在床榻上,被子上都是她吐的血,她连最后一句都没和我说完,我便被阿爹卖入了花楼。
可能是在花楼中也吃下了不是偏方,我身下的血像是止不住一般。
渐渐的我没了呼吸,等老爷回来时,直呼晦气,一卷草席就将我扔了。
我一生从未做错什么,可惜遇人不淑,父亲将我卖入花楼,我伺候过几个花娘,也做过花娘。
最后被赎出后也逃脱不了做暗娼的命,我生来一身血污,死后也是一生血污,注定不能清清白白。
这便是我的命,我也只能学着认命,我只希望珂珂能一生顺遂,不必再颠沛流离。
一九七三年的猪
文/周 龙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我未满十一岁,刚上小学四年级。
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正躬着身子,在门口忙碌地编结猪笼。父亲把刚编好的六个小猪笼码在门边,然后对我说,明天跟我去赶下坳街。我说,做什么?他说,挑仔猪去卖!我立马跳了起来,惊喜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就能看见街上熙熙嚷嚷的人群,看见百货商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真是太令人期待了。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一二辆穿街而过的班车。要是父亲高兴,兴许还能给我卖一两颗纸包糖呢。对于山沟里的娃仔来说,这绝对是很奢望的一件事!下坳是与我们大兴公社相比邻的另外一个公社,据说下坳街要比大兴街宽大得多,也热闹得多,各种生活用品摆满整条大街。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去赶一次下坳街,从那里挑回红薯、木薯、玉米,给我们全家九口人做口粮。下坳街简直就是我们全家人生存的福地。
想到第二天就要去下坳街,我兴奋得一夜都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幅幅地虚拟着下坳街的场景,商店、饭店、粮所、猪市、肉行什么的,琳琅满目,总之,要比我见识的大兴街要牛得多!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我刚刚睡着了一下,父亲却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我揉揉婆娑的睡眼问道,走这么早?父亲说,早什么早,晚了还赶个屁街?母亲早早就起来了,煮了一锅玉米糊,还喂了猪。父亲把六头仔猪装进猪笼后才叫我起来的。我迷迷糊糊地刨了两碗玉米糊,就挑着仔猪跟父亲上路。我挑两只,父亲挑四只。柔和冷静的月光下,父亲象棵会走动的树游走在我前面,我象树的影子紧跟在后面。走的是山路,一个峒场接一个峒场地穿越,父亲走得飞快,我紧赶慢赶才勉强跟得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到哪里了,反正就是走。冷硬的山风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脸上、耳朵上,疼得麻木不仁了。笼子里的仔猪估计是困倦了,难受了,一边喘息一边噢噢鸣叫。大约走了两个钟头,天开始亮了。走到一个叫安福的村庄,道路开始平坦,我们停在路边歇息。父亲打开那只挂在猪笼边的小布袋,拿出两个干巴巴的玉米窝窝头,递一个给我,他津津有味地啃着另外一个。我身子有些发飘,口干得不行,根本啃不动。父亲催促道,快点吃!我说吃不下。父亲说,吃不下也要吃,要不饿死你!我努力了一下,只咬了一小口,很干,很硬,很久才吞得下去一小口。我把窝窝头递给父亲,父亲把它放在布袋里,在沟边捧了一口生水来喝,我也学着他喝了一大口,呛了好几下。我们继续赶路。父亲几乎是小跑着,我跟本跟不上。父亲只好停了下来等着。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又接着小跑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催道,走快点走快点!好像有人撵着我们的屁股一样。大约又走了两个小时,我们又停了下来,父亲继续吃着又干又硬的窝窝头,然后在沟边喝生水,我也只剩下喝水的力气了。父亲的速度依然飞快,而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父亲不耐烦了,骂骂咧咧的。死呀你,走这么慢,等到了下坳,街上的人都散了,还卖个屁猪!后来,见我实在走不动,父亲就逼我走在前面,他的脚步嘚嘚嘚撵在我的脚后跟,他的猪笼一直顶着我的屁股。我不得不拼命地往前迈步。后来,见我走得实在太慢,他又走在前面带着。我的双腿都已经迈不动了,父亲却仍在小跑。他的膝盖好像装上了钢玻珠,运动自如,永远都跑不累。
昨天傍晚,答应父亲来赶下坳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体力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两年从早到晚挑水粪的经验。我差不多九岁的时候,父亲给我编了一对小小的粪桶,差不多是父亲那对大粪桶的一小半吧,能装三十来斤的粪水。放暑假的时候,正是抢种玉米时节,我挑着满满当当的两小桶粪水跟在一排挑着大桶粪水的大人后面,不停地奔走在粪池和玉米地之间的山路,从早挑到到晚,几乎没怎么歇息,我也从不拖大人们的后腿。因此,大人们毫不吝啬地表扬我:天啊,这么小的个儿都能挑成这样,以后长大了,要多大的粪桶才够他挑啊!这话让我心里堵了好长一阵子,感觉怪怪的,好像我这辈子专门是为挑粪而生的,好像除了挑粪,我这辈子什么事都干不了。父亲却没有我这种感觉,每次听到这样的表扬,父亲便高昂着头,嗯嗯嗯地哼着鼻子。那得意劲像是培养出多么了起的挑粪接班人似的。但是现在,这个接班人让父亲大失所望。他把我甩开一段较远的距离之后,把担子从肩上卸下来,站在原地朝我招手,嘴唇不停地咕哝着我听不到的话语,估计是在叫骂:该死的,就知道吃吃吃,一点屁力都没有!平时他骂我们兄弟几人,就是这么个腔调。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我们多喝一口稀得看见碗底的玉米粥,父亲就会咬牙切齿,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扫射我们。现在,虽然我听不到他的骂声,但他一定是这样叫骂,每次我们干重活叫苦叫累,他都要会这样骂,没完没了地骂。我在听不到父亲的叫骂中拼命往前赶,走近他,然后在他清晰的叫骂中走过他前面。这时,他会重新会挑起猪笼,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我,然后放下猪笼等我,叫骂我。就这样,一下子他在前面,一下子我在前面,走走停停,我在父亲的叫骂声中拼命地往前追赶,一刻也没敢停下脚步。
正午一点多,我们终于达到下坳街,进入猪市,放下笼猪,我两眼一闭,就团软在地上,全身象散架的样子,动弹不了。直到父亲大叫了一声,快点站起来,有人来买猪了!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睁眼一看,果然有个中年男子在猪笼旁边转来转去。他一个猪笼一个猪笼地翻过来,翻过去,摸摸猪的耳朵、嘴巴、尾巴、肚皮,他甚至还用手压了压猪的后背。他对父亲说,六块,买不买?父亲摇摇手说,少七块不卖。那人摇摇头,走了。我问父亲,六块一斤,很贵了,还不卖呀?父亲说,做梦吧你!六块一头,贵什么贵?我愣了一下说,不称斤呀?父亲说,下坳街都这样,论个讲价。后来,还有两三个人过来问价,听见父亲说少七块不卖,人家连看都不看就扭头走了。站在空空荡荡寒风凛冽的猪市,我的身子一直发颤,心里不停地叫道,快点有人来问呀,快点卖掉呀。下坳街是个赶早的街,过了下午两点,赶街的人就陆续散场了,上市的猪都被人买走了,猪市就剩下我们的猪没卖掉。头一个来问价的男人又走过来对父亲说,六块还不卖?我用脚尖磨着地板,心里着急地说,卖得了呀,卖得了呀,赶紧买呀,我差点说出声来。谁知道父亲却坚决地摇摇头,好像这天他只会摇头,那人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人又来到猪笼旁边,他竟然问了句五块卖不卖?我父亲瞪了他一眼,恶劣地吐出两个字:神经病!那人也不示弱,把“神经病”三个字又恶劣地仍回给父亲,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之后,再也没人来问价,猪市就剩下我们父子俩和六头困在笼子里的仔猪。父亲背着手,来回张望,一脸的无奈。又等了半个时辰,父亲拿起扁担把猪笼串起来,说,走吧。我说,去哪儿?猪还没卖呢。父亲说,卖不落了,挑回家!我眼前一黑,心里叫了一声,我的天啊!我说,我饿死了,走不动了。父亲骂道,再不走天就黑了,你想死在这里啊?我挑起猪笼跟在父亲后面走出猪市。
走到街上国营饭店门前,我把肩上担子放了下来,哆嗦着身子地对父亲说,我想吃米粉。父亲瞪大眼睛,吃米粉?猪卖不落,吃个屁!我说,我饿死了。说着就团坐在地上。父亲从布袋里拿出一个干硬的窝窝头递给我说,吃这个。我说摇摇头,我吃不下,我要吃米粉。父亲咬着牙,做出要踢我的样子。他三下五除二把窝窝头啃光了。然后,一手伸进上衣口袋,翻出了五斤原粮(粮票)和1角钱。父亲对我说,看好猪,别走开哦!说着父亲就跑进了饭店。几分钟后,父亲摇摇头走了出来。我说买得了?父亲说,得个屁,人家不要原粮。我说他们要什么?父亲说米票。农民去哪儿要米票?那时,农民卖了玉米之类的公购粮,粮所只发给原粮,干部和老师才有米票。原粮要等到荒月的时候,才能凭指标到粮所去买玉米、木薯和米糠,而米票却能买回大米和面条。父亲急猴猴地说,走吧走吧!别吃了!我赖在地上不动,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父亲猛瞪了我一眼,威胁道,再不走,天黑了你就死,你走不走?我有气无力地摇头,说饿都饿死了,我真走不动了。父母破骂一句没用的东西,就朝着公社方向走去。半个小时后,父亲匆匆跑回来,扬着手里一张票子对我说,五斤原粮跟公社干部换来的一斤米票。父亲用其中三两给我卖了一碗素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拌了酱油的米粉,简直热血沸腾了。我用筷子一根米粉一根米粉地夹起来,放到鼻孔边使劲闻了又闻,然后吸进嘴里,很慢很慢地吸进去。每吸完一根,就伸出舌头,舔了舔粘在唇边的汤迹,然后再吸第二根。虽然坐在边上啃玉米窝窝头的父亲一再催促,吃快点吃快点,我依然慢慢地吸慢慢地品,让那香味从嘴里一路滋润下去,真是太享受了!有了这碗素粉的激励,那天,几乎已经摊痪了的我重新振作起来,挑着那两头快要饿死的仔猪,拼命地跟在父亲身后,拼命地奔跑着,回到家已是黑咕隆咚的深夜。我一进门就倒下,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全身几乎所有的关切都肿胀,酸疼。我软绵绵地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三天后才能下床走动。
一个星期后,因为猪食短缺,也因为急用钱来买一家人的口粮,那几头小猪被迫卖给临村的两户人家,价钱比下坳街贱了不少。上称之前,几头小猪竟然齐唰唰地洒尿拉屎,少重了三四斤,把父亲气个半死。他抬脚狠狠踹了一头仔猪的屁股,咬牙切齿骂道,该死的!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